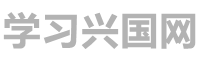“刘琅:周树人周作人之家事与家财”
鲁迅住在八道湾的时候,起初每月工资不缺,比周作人还多,忠实地交出了所有的东西,也兼顾了向朋友诉说。 这样的人,在家支出是得力助手,是必要的。 之后开始欠薪,干涉人事方面,会损害主人的权威,变得讨厌。
于是鲁迅搬走了,用鲁迅自己的话,被赶出了八道湾。 日记上写着,1923年7月3日,在弟弟和东安市场等地,7月14日开始在自己的房间吃饭。 这也是值得记住的话。 7月19日上午之前,启孟带着信来,约我稍后再问,没有来。 周作人亲自寄来的信中,外面写了鲁迅先生,信中除了同样的称呼外,开头的句子是我昨天第一次知道的… … 从这些话中,倾听他人的话一点也不怀疑。 鲁迅必须追问情由,但周作人却毅然决然。

周作人自己的态度到底怎么了? 后来,我听说鲁迅解体事件的经过,周作人曾经和信子闹过,结果她比他还闹得厉害。 从此,周作人认为,要在家中寻求安宁,也必须不惜哥哥的牺牲。 两者相权是比较有利的。 但是现在哥哥可以卖钱,可以写哥哥的案子也可以投机,吸死人也可以营养自己的身体。 要说哥哥怎么办,那是骗人的把戏,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鲁迅躺着突然来了,带着连日患病的牙痛,搬到砖头巷暂住到8月2日。 期间,又带病看家,另找住处,然后妈妈又病了,又陪着看病。 到9月24日,鲁迅真的病了。 24日咳嗽,好像中寒。 第二天晚上又吃了三粒药出汗,10月1日发烧,用阿司匹林出汗,又腹泻了4次。 但是,同样去讲课,我记得10月8日又用《中国小说史略》的稿子发给孙伏园,然后也教、看房、看病,到11月8日晚上喝汾酒、喝粥 到了1924年,鲁迅经肋痛,校医云是轻症胸膜炎。 3月间好像在闲荡中生病,想在闲荡中作文也做不到。 但是,在4月的日记中,除了日常的工作之外,还看到了季节最后在《小说史略》的讲义上印刷了书,全部完成了另一个工作并传达给了朋友。 再次看房修缮,重新开始经营后,在1924年5月25日星期天晴朗的早晨,移居到西三条胡同的新家,并记在日记里。

6月11日的日记下午,与其去八道湾家拿书和什物,进入西厢,不如启孟及其妻子突出破口大骂,还打电话叫来了重久、张凤举、徐耀辰。 妻子说了我的罪状,说了很多脏话,如果捏造了圆不圆的地方,启孟就会救正之。 然后终于拿起书出去了。 这个廖数语,也可以推测大致情况。 其实除此之外,据鲁迅说,当看到他们来势汹汹,向朋友求助的态度时,鲁迅说:“这是我周家的事,别人不介意。” 张,徐在这里走开。 周作人竟然手里拿着一尺高的铜香炉,向着鲁迅的头打,被别人抢走了,才打不中,这时候又数了几个毛病。 鲁迅那时回答了。 “你说我很多人都不一样。 我在日本的时候,你们俩每个月光靠留学生的微薄费用是不够的,所以回国工作帮助了你们。 这个终于好了。 那时周作人挥手说:“鲁迅学做了手势。” “至今为止的事不算! 就这样骚动开始了。

之后鲁迅被赶出八道湾后,常常感叹地说。 “我被赶出八道湾真是太好了。 生活必须有预算,生活也不困难了。 鲁迅经常自己借钱维持整个大家庭的支出,如果节约一点,不是可以更少向外借吗? 有时欠债辗转他人,来银行放高利贷。 在这里,我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为哥哥无法偿还的债务而生活的痛苦生活方式,我觉得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老实人,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鲁迅当时所想的也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说:“自己的负担很轻,如果他们需要用的话,交给他们就行了。” 鲁迅除了负担八道湾的大部分家庭外,还有日本人信子他们的父亲羽太家:每月的家庭援助,儿子重久三次在中国和日本的随时需求和军营的必要费用,以及第三个女儿福子的学费,都是鲁迅每月领工资,很快就汇了出去。

茶后,鲁迅又曾随意地感叹自己遭遇的经过。 他悲伤地描绘了他的心情。 “我一直认为,即使别人不给钱,家庭也能圆满吧。 住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工资收入全部交给了两个妻子(周作人的女性,名信子)。 连周作人都不到600元,每月还不够。 向朋友借一下,有时借一下手就回家。 又看到车从家里出来,我被黄包车运走了,怎么能开车带走呢? 因为家族里的人不断得大小轻重的病,鲁迅总是要请医生来,鲁迅忙着应对这些工作。 没有计算过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那么,他们每月六百左右的收入(鲁迅三百,周作人二百四十),除去稿费,去了哪里呢? 鲁迅说。 “她们一有钱就又去日本的商店买东西了。 不管紧急与否,我都大量买了它。 从食物、用的、玩的、腌罗姆人到玩具,很快就花光了。 控诉没钱了,不得不借钱生活。 有帝国主义者剥削一样的态度,她们的心向着日本,要照顾日商。 中国人的家庭,她以奴隶的姿态出现。 他们用一个叫徐坤的总结者,这个人很精明,什么事都能处理好。 例如,周作人父子共有3辆黄包车,其车夫的招聘和工资经过徐坤之手,周作人买鞋、订大衣也是徐坤让人做的,从而获得巨大的利益。 这是旧北京人的旧习性,众所周知。 不仅如此,徐坤的家人,住在隔壁,隔着矮墙。 鲁迅住在最开始进去的外面的房子里,每天上班前都会自己看徐坤从墙上把食物送出去。 鲁迅仔细一看,有一次向执事的两位夫人讲述了这不平凡的寄生生活的情况。 信子叫徐坤,不是骂徐坤,而是说:“你为什么要给他(鲁迅)看? 能做这些事,就是说瞒着鲁迅就好了。

有一次,小孩子在窗外玩火,几乎着火了,被鲁迅发现很紧张,觉得应该训诫一下,她们听了很不舒服,好像玩火没问题,不被鲁迅看到就好了。 在鲁迅,辛辛苦苦建造的新居,是花了无数心血、不可估量的劳动才完成的果实,自然受到珍惜。 即使对普通人来说,没有人看到孩子玩火就不禁止。 她们没有脏腑行动,鲁迅在哪里能预料到? 这些日常琐事,也许是为了进入资料,周作人视而不见,整天拿着书,其他一切都可以放入精力和浪费时间等解决生活方式中,也成为每天的分歧点。 鲁迅还提到周作人经常在孩子身边哭,能平安读书的好空气量,他说如果是我就不会。

周作人的人生哲学另有一套。 他告诉别人,他知道徐坤贪污后,如果换了徐坤,要求他自己做日常工作(例如自己的服装等),就必须减少读书的时间。 所以他不是不知道徐坤的不好,而是要是能在不好的情况下处理他的问题就好了。 其实还是以讨厌劳动的旧知识分子的态度,专门剥削别人的劳动。 对鲁迅也一样。 鲁迅辛苦的经营,他在哪里能体会呢?

这不是冤枉了他,事实证明。 人们只要打开鲁迅的日记,1919年,鲁迅就匆匆看了一眼房子,最后找到八道湾,然后又修了房子,第二天去监督,联系警察局,谈判,领合同等,付出了很多心血,还到处借钱,银行 他今年3月从北京大学请假,和家人去日本玩,中途回了北京,几天后又去了。 在新屋成交之前,鲁迅先租了几间房子,粉刷,准备家具,包括周作人的家人和日本妹夫重九在内,一大批人光明正大地回到了北京。 如果说周作人也用过劳动力的话,确实如此。 我去警察局拿了一张住宅合同。 这可能是因为他要花时间和精力去写吧,但是朝着日本跑,不是不花时间和精力吗?

关于这个房契,也有以下的故事。 鲁迅不自私,本来立房契的时候,他就像写文案用兄弟的名字一样,要写房东是周作人的户名,但是被教育部同事说服用周树人的名字,把鲁迅赶出了八道湾。 周作人本来在绍兴卖祖屋的时候,要分钱花,但多次被鲁迅买回北京。 那样的话,他们至少有什么适合居住的地方打破了他的计划。 这是为他们着想的好意,但看钱就花,不在意时间的长期周作人不管这些。 这个时候,又恢复了旧状态,八道湾屋也必须卖掉。 风声传到鲁迅耳朵里,说:“卖得好,但我也得分一份。” 这时候鲁迅想起了教育部同事的预见。 用了周树人的户口名不是那么容易卖掉的。 鲁迅如果活一天,必须在他最初签名后卖掉。 这件事还搁置了20多年,鲁迅在上海逝世后,周作人干汉奸,威吓了一会儿,他把房契改成了他自己的名义,是他的。 根据例子,应该没收后归还给公众。 但是,政府的慷慨,给他窃取的方便了。 这是后话。 也可以解答一些人的意见。 我认为他们兄弟不和的原因是物质关系。

鲁迅出走后,信子从此更加蛮横,而周作人自然做出了更多让步。 即使友爱的哥哥牺牲了,其他人也不像话。 经过这样不光彩的斗争软化为信子后,更向敌人投降了。 国事和家务都一样。 沿着这条路线走,鲁迅说:“她们(刚从日本回来,住在绍兴。 那里没有领事馆。 她们还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发泄怒气,至多装作醉死。 有一次,她的兄弟在重久身边,拆散了她的装腔作势,不理睬她,说自己要起床了。 正是这样,才是长久以来家人对她束手无策的魔术。 一到北京,她就跑过日本领事馆,都请日本人教,一听到风声就把日本旗扯下来了。 她们害怕日本不会侵略中国,日本来了,她们有好处。 周作人解决家务也嫌麻烦的性格,让眼前的利益迷失了他的方向,成为高级官员(假的),有工资,还兼有促进女性自动避难的作用。 并且,为了应付当场,将民族利益轻于个人利益而以汉奸告终,这是他们兄弟俩各自特殊行为的一大领域。

换个话题,兄弟不和之后鲁迅在上海,人们常说周作人的复印件可以读。 他确实如此。 因为兄弟的不和,把他的作品都抹杀了。 周作人每产生一部新作品,出版一次,他一定会买来读,有时也会约在一起读。 如1928年9月2日,在日记中也是下午和三个弟弟去了北方的新书店,为广平买了《谈虎集》的上一本和《谈龙集》的上一本。 另外,1932年10月31日,买了一本周作人散文牌。 这表明他伟大的胸襟,在文学上以个人关系不夹杂私情,纯粹从文化上考虑。

据鲁迅分析,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周作人态度还不错,和大家一致向黑暗势力战斗。 因为没有直接威胁到他的生活。 到1926年9月,女子文理学院又第二次被任命为任可澄教育总长,与林素园校长同率有警察厅保安队和军警部处的兵卒四十人左右,驰跑去了女子师范大学,武装接管。 参见《华盖集续集》。 (到了学校强烈指着徐某说共产党,当场又要逮捕他的时候,周作人考虑到身边的利害,不敢再战斗了。 在《语丝》96期《女师大的命运》的复印件中,言明=周作人说:“曾经解散过一次的师生很幸运。” 意思是,被留下来的人很不幸。 不幸的是,如果流亡生活不愉快的话,只能按照当权者的意向行动。 个人现在衣食无忧,可以免受政治(汉奸占领的局面)的压迫,作为后来下地狱的菩萨装扮自己,总会上日本人的手,用诉说无罪的苦心撒谎,请人们理解并自嘲 一个不仅仅是个人,一个都是大众,只有距离稍有不同,总账却非常大,正是霜降的坚冰,其由来自有。 鲁迅还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有幸来到南方,看到和学习了很多有意义的教育,如果还留在北京,就看不到那么多东西。 但是,周作人对人说: 我不去南方,我怕鲁迅的党羽(指作为左联人民的作者)攻击我。 暗老鼠看不见光,自由自在地胡说八道。 (许广平《回忆录》笔记) )。

译文:百韬网
本文:《“刘琅:周树人周作人之家事与家财”》
心灵鸡汤:
免责声明:学习兴国网免费收录各个行业的优秀中文网站,提供网站分类目录检索与关键字搜索等服务,本篇文章是在网络上转载的,星空网站目录平台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只为传播网络信息为目的,非商业用途,如有异议请及时联系btr2031@163.com,本站将予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