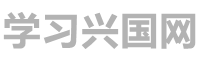“在东西两洋间重述“中国”:近代日本的东洋学/中国学”
[领先]亚洲的中国或中国和亚洲是相互关系的结构。 中国需要在具有众多复杂文化历史和众多民族构成的亚洲不断明确自己的位置,而且变动中的亚洲也不断认知和接受中国的快速发展。 本文以1945年日本战败为界,分为两个时期,概述了日本近代东方学/中国学的起源和迅速发展的脉络,并对日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地缘政治背景下如何定义和论述中国,为今天思考亚洲-中国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思考资源。

目前,亚洲毫无疑问是当今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心和世界政治的首要焦点之一。 其中,中国在该地区地缘政治中占据核心位置,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巨大而迅速的发展前景。 但是,对于这片广阔的土地和宗教历史错综复杂的地区,我们到底知道多少呢? 暂且不说国家战术和政策制定的水平,思想学界是否已经具备足够的亚洲意识,人文科学研究对亚洲地区的积累能否支撑起重新定义中国与亚洲关系的意志和实践。 这些还是值得怀疑的事情。 事实上,近代以来亚洲-中国曾多次被重新定义,但我认为影响历史快速发展趋势的只有三次。 首先,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列强殖民扩张渗透亚洲之际,西方人包括革命前后的俄罗斯领导人对亚洲和中国的重新认识。 其次,作为该地区内新兴帝国的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以新的地区盟主的姿态重新关注和论述了亚洲和中国,为之后的海外扩张铺平了道路。 第三,新中国创立后的毛泽东及其社会主义中国的三个世界和亚洲社会主义构想。 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说,前两次是被动的话,第三次是新生中国主动面对世界做出的自我定义。

上个世纪,西方、日本乃至中国自己对亚洲-中国的论述呈现出极多复杂的形态。 其中,不仅为帝国主义殖民战争提供合理的知识生产,还包括世界革命理念下的对亚洲—中国的认知重组。 今天,我们面临着重新定义中国与亚洲关系的现实挑战,但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我们提供想象力和思想资源。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和亚洲社会主义构想是意义深远的议题,但我一直认为它只停留在社会革命和世界战术的理念层面,不以广泛而深刻的文化历史知识的积累为基础。 换言之,这一理念没有得到人文社会科学一个部门——区域研究亚洲论述的比较有效的支持,我们在新中国以后的学科建设中受到科学快速发展和国力局限,亚洲研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到今天这种情况也没有根本改变。 因此,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到改革开放的建设阶段,这一具有深刻意义的构想也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

比起西方,始于19世纪后半期的日本对于亚洲-中国的知识生产,有着深刻的思想学术和文化历史的广度。 这是因为日本也属于亚洲地区,不仅现代化最先实现,战前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国家战术作为政治推动力,战后基于反思现代性和侵略历史的强烈意识,形成了认知中国革命和亚洲替代现代性的大视野。 日本已经形成了关于亚洲地区研究的系统性学术传承,可以说至今仍是生产中国和东亚知识的世界重镇。 本文概述了日本近代东方学/中国学的起源和迅速发展的脉络,以1945年战败为界分为两个时期,论述了在亚洲广阔的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背景下如何在战前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学,战后参照中国革命提出了新的亚洲论述 我认为这些不仅能为我们提供相关知识的参考,还能促进我们思维方式和认知视野的转变。

二七十年:从战前的汉学/支那学习战后的中国学
明治维新至今已经走过了150年的历史,其中以1945年帝国日本的崩溃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70年。 关于亚洲-中国的知识生产,也受到战败这一历史性剧变的影响,显然有前后两个时期。 这种区分首先出现在学科的名称中。 众所周知,战前的日本把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研究称为东洋学,研究中国的学问是汉学(东京)或支那学)京都。 如果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的汉学继承了明治国家忠君爱国这一儒教意识形态,继承了此前传入日本的汉学之名,那么显然具有为国家服务的官学色彩的话,以京都帝国大学为中心的支那学就是清代考证学和悠悠学 但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和亚洲的广大地区推进殖民扩张战术,即使是这个京都学派也未能幸免于被战争意识形态污染的命运。 例如,中国社会停滞论、东方专制主义等,曾经是讨论中国历史的基本认知,不是东京的汉学,也不是京都的支那学。 另外,东方文化中心移动说,也就是中国文明已经衰退,其文化中心开始向东移动到日本(内藤湖南),这是个别学者的观点,但也表达了中国为了落后的保守,日本应该指导其改革的理论根据,成为日本征服中国的逻辑依据

因此,二战以后,在日本人自身反省侵略战争的意识推动下,新生中国于20世纪50年代初向日本政府提出查询,要求不采用带有侮辱和歧视意义的支那语,因此,日本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改为中国学,位于大学教育学科中原的殖民政策学也改为地区研究。 这当然不仅意味着名称和学科的变更,也意味着日本战后关于亚洲-中国的知识生产的基本角度和学术倾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追溯日本近代的亚洲中国知识生产之际,我们应该关注学院内的汉学/支那学,也应该观察学院外的中国论述。 第一,它由与信息媒体有关的中国问题的注意者和长期居住在大陆、知道中国革命并与之同情的日本人,即在野学者承担。 他们置身于波涛汹涌、动荡不安的现实中国,努力关注着众多肮脏的中日关系,乃至亚洲和世界的大势。 其研究明显不同于以古典中国为首要对象,学术传承中可见谱系的学院派。 而且,他们又与日本的亚洲战术密切相关,这也常常摆脱不了帝国主义国家意志的笼罩,成为大陆政策的建言献策者。 同情孙中山革命的大陆浪人宫崎滔天,半生隐居北京,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书闻名的中江丑吉、鲁迅素有一面之识,因《支那社会研究》《支那思想研究》去世的橘朴,以及深深关注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尾崎秀实,直接投身于20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而闻名。

如果关注学术背后的权力政治,就必须意识到战前日本的汉学/支那学与该国的密切关系。 20世纪70年代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全球国际体系时代,原有的东亚地区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和两大对外战争,成为了新兴的帝国和地区内的中心国。 然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满洲事变,彻底走上了大陆经营的国外扩张之路。 这种称霸世界的国家战术的形成,有力地刺激和带动了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 其中,特别是关于亚洲中国的知识生产取得了惊人的成果,20世纪上半叶形成了与欧洲中国学抗衡的鼎盛势头,同时也未能幸免于隐藏的殖民色彩,以及宗主国关注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视线。 也就是说,学术上的辉煌成就和帝国主义知识生产的性格都有,构成了日本近代汉学/支那学的极其繁多的知识形态。

而且,战后日本的亚洲-中国研究在上述对帝国的知识帝国化的过程中沐浴而脱胎换骨。 这里,有两件值得注意的学术事情。 一是1946年,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历史学家齐聚一堂,成立了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实现了战前西方史、东洋史(中国史)、日本史三分天下格局的重组。 新生历史学研究会在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提出中国史是生产形态快速发展史的概念,反思战前的东方社会——中国停滞论。 这一争论随后迅速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学派与继承内藤湖南唐宋变革学说的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等的争论。 虽然争论没有形成统一的见解,但无疑促进了战后中国历史研究新局面的出现。 而且,京都学派的中国观也取得了新的迅速发展。 例如,宫崎市定的《亚洲史概说》、《中国史》等。 小岛祐马在1950年出版了《中国的革命思想》、《中国共产党史》两书,这象征着随着时代的变化,战前京都学派的重镇也开始着眼于现代中国,实现了该学派的中国学的重新铸造。

另一个是1948年成立的日本中国学会和1953年鲁迅研究会的出现。 前者是全国性的民间学术团体,反省了战争重建中国研究学科的时代要求,聚集了日本对中国文化、思想、文学等各学科的研究力量,以中国的名义深入探讨了学会以及前支那研究的问题,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化、革命思想、人民文学的研究。 后者是以东京大学中文系学生为中心成立的小研究组织,他们通过鲁迅文案的解读感知中国革命和现代史的迅速发展,反思日本的近代化,揭示了战争中竹内好、武田泰淳等创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从前流传下来的,在文学史知识积累方面超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不足和缺点。 这两个规模不同的研究会从重视中国革命和现代文学思想的以前流传至今。

战后日本的中国学,在东西冷战冲突的世界大背景下,从亚洲的历史语境关注中国,或者通过中国革命重新思考亚洲的现代性问题,摆脱日本政治上依赖美国与侵略战争迫害的邻国无法和解的被动局面,论述独特的新亚洲主义 这种新亚洲主义以反思西方现代性、追求亚洲殖民地的真正解放为思考目标,与战前的亚洲主义明显不同。 日本进步的知识界,特别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们,在反对1950年代旧金山和约的单方面媾和和1960年代日美安保协定的斗争中,痛感日本在美国新殖民主义下被殖民的危险性,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第三世界开始 在此基础上,中国被重新定义,其革命典范意义得到高度肯定,成为战后日本中国学的一个亮点。 例如,日本古代史的石母田正、西嶋定生、近代史的远山茂树等重视从东亚的角度关注历史问题,中国研究界有竹内好等提出以鲁迅、毛泽东的革命为典范的新的亚洲原理。

那么,战前和战后两个70年的日本中国学,在怎样的思想视野和逻辑结构中重新定义了亚洲和中国呢?
在东西两洋之间定义亚洲
众所周知,通过明治维新推进现代主权国家的构建,日本在不足20年的1880年前后取得了制度建设上的重要成果,其中兵制改革( 1879 )和国民教育体制的确立) 1881 )最为重要,因此成为后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国策乃至海外扩张的国家战术 以前流传下来的汉学是近代的中国研究,其学科体制的完善也从现在开始。 从幕末到维新,经过兰学的进口和黑船来航事件等,日本人在与欧美的接触中已经打开了视野和视野,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以前流传下来的华夷秩序观及其下形成的汉学由以前流传下来而衰退,新的世界观念和亚洲的想象逐渐形成。 在东西两洋之间重新定义亚洲,重新思考中国在亚洲的想象,首先体现在国家教育体制的学科修改上。 日本蒙古史研究的先驱那珂通世于1895年在高等师范学校创立了东洋史学科,将其与本国史(日本史)和西洋史并列,开创了战前日本教育体制中将支那史定位于东西两洋之间的先河。 他1890年出版的《支那通史》全四卷,实际上是在参照欧美历史教科书的基础上,进行了使以前流传下来的汉学脱胎换骨的重组。 其中,历史事实的客观描述和科学实证的研究做法以及中国文化停滞论,构成了这本书的基本特色。

关于大学教育体制的学科修改是10年后。 例如,京都帝国大学于1906年创立文科大学(文学部),为了与东京帝国大学抗衡,开设了分别属于哲学、史学、文学学科的支那哲学、东洋史学、支那文学三个讲座,体现了大学创立之初重视东方学迅速发展的方针,是京都支那学的基本。 其中,东洋史的名称值得观察。 内藤湖南强调东方史即支那文化的迅速发展史(《支那上古史》绪论),但在学科建设中多次使用东方史的名称,显然是要重新定位中国。 另一方面,东京帝国大学在1910年将支那史学科改为东洋史学科,作为学科的东洋史学其制度最终确立。

总之,20世纪初日本已经建立了新的汉学/支那学知识制度,中国在西方、东方、日本三级结构中被重新定义,中国史常常被涵盖在东方史上,原有的权威地位和世界意义相对化,成为亚洲地区内的地方性知识。 东洋史吸收了从以前传下来的日本汉学,确立为以中国史为中心,包含亚洲各民族各国历史文化的学科。 其时代背景在于,日中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促进了日本人亚洲意识的觉醒,诞生了与西方学不同的东方学。 其中,从对抗西方到联合东亚到征服亚洲,日本的国家战术在学科的快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然,这个东洋学的核心依然是中国学,但是战前也有东京的汉学、京都的支那学之分。 以以东为中心的汉学,贴近国家意识形态,通过儒教确立忠君爱国的道德伦理秩序。 学术成果突出,但维护儒教、为国服务的政治倾向,乃至以儒教统一亚洲和世界的意识形态狂想,在今天无疑是落后的保守有害的。

相比之下,战前京都的支那学也未能幸免于被战争意识形态污染的命运,但其一再纯粹学术的基本态度无疑推动了中国研究的迅速发展。 他们也同样经历了将中国知识相对化地方化的过程。 但是,京都学派在强调新的世界观的同时从外部关系重新定义中国,也着重于狩野直喜尊重中国人的价值观从其内部注意历史的态度,以及内藤湖南等人对章学诚和清代考据学的重视和发掘等中国内部的历史规律和做法。

具体来说,今天我们称为京都学派的,是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文学部)第一代校长狩野直喜( 1968~1947 )等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学构想的开始。 之后,形成了以内藤湖南为首的中国学派和桑原隈藏开始的东洋史学派,形成了两大潮流并行迅速发展的局面。 其中的中国学派有狩野、内藤等东方史和中国文化史研究以及铃木虎雄、青木正儿等中国古典诗文研究,有两个学术方向平行迅速发展的现象。 京大中国哲学史研究也由狩野直喜首创,其学术特点是构建基于清朝考证学的文献实证研究。 另外,这是小岛祐马( 1881~1966 )通过将思想视为社会的产物,引入社会科学来考察哲学的历史意义的社会思想史研究。 也就是说,小岛祐马和狩野直喜一起从京都学派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以前就流传下来了。 另一方面,如内藤湖南( 1866~1934 )的唐宋变革学说,中国近世始于唐末宋初,但东方在千年前就已经有自己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了对抗西方学术界亚洲未产生资本主义因素的历史叙述,中国近世的根据和做法是汉魏六朝的政治 铃木虎雄( 1878~1963岁)自始至终立志讲授中国诗文,影响了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中国文学艺术研究家的出现。

另一个亚洲、世界视野下的中国论述[/s2/]
以上,笔者首先考察了战前日本学院派汉学/支那学迅速发展的概况,在观察中国相关知识生产内在的、挥之不去的帝国主义殖民色彩的基础上,阐述了在新的世界观念下,在东西两洋之间重新界定亚洲,重新审视中国的学术发展过程。 那么,战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确实,1945年的战败和帝国日本的崩溃引起了历史的严重断裂。 但是,这种断裂体现在政治经济的制度层面,思想学术在战后仍有新的面貌和快速的发展路径,但与战前批判性继承的关系却很淡薄。 东京的汉学、京都的支那学和战后的中国史研究的关联就是这样,战前日本学院派以外的中国论述和战后迅速发展的中国革命研究的传承关系就更不用说了。 以下,笔者仅略谈战前两位杰出的中国论者橘朴、尾崎秀实和战后竹内好等的继承关系,探讨日本学者在另一个亚洲、世界的视野下如何论述中国革命及其亚洲的意义。

橘( 1881~1945岁)被认为是日本战前最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日俄战争后,他来到中国在京津大连等地居住了30多年。 在此期间,他亲身经历了现代中国激烈的社会革命和历史变迁,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记述。 1936年出版的《支那社会研究》、《支那思想研究》是其前半生文案的凝聚,不仅有对国共两党社会革命的考察,而且其研究从民间道教延伸到中国社会性质,形成了关于中国的自足解释框架。 其中,下层广大民众的思想信仰(通俗道教)和上层社会的阶级关系)官僚阶级统治论)和下层社会的自治组织形态)是贯穿社会历史多个层面、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系统,可以从中得到关于中国的总体记述

朴自称为在野的布衣学者,与学院派的汉学/支那学学者不同。 他注意到中国的视野在于实际的社会革命,以中国人的尺度为基准评价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迅速发展。 他反复批判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对中国的无知和轻蔑,同情中国革命,努力确立自己独特的中国论述。 但是,橘朴是一位多而杂的历史人物,其思想认知有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 满洲事变前后他发生了方向转变,从在野的平民投身日本国家,成为提倡王道的伪满洲国建国理论家。 这将满洲国王道自治论和东洋共同社会论等他后来在中国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东亚社会的知识构想作为对日本殖民扩张行为的理论论证。 也就是说,后期橘朴试图在因日本殖民扩张而发生巨大变动的亚洲地区重新定义中国,并在大战爆发后提出了东洋共同社会论。 他阐明了印度、中国文明的伟大和日本平等联合的必要性,但多次日本人会在融合东方各文明中发挥指导作用吧。 因此,他的带有反西方资本主义好处社会的东方共同社会论,不可能不带有右翼意识形态的色彩。

如果说橘在后期亚洲尝试重新审视中国是失败的尝试,与他前期研究中国的成果一起被遗忘了,那么同样是日本战前杰出的中国论者尾崎秀实( 1901~1944 )关注社会革命和亚洲社会主义理念构筑的现代中国的做法论 尾崎秀实是参加二战期间轰动一时的索尔盖红色国际谍报团,1944年被日本军国政府绞死的传奇人物。 但是,在笔者看来,他的历史功绩不仅表现在参加佐尔格国际谍报团上,还表现在中日战争时代发表的许多出色的中国论述上。 那部《暴风雨中的支那》、《现代支那论》等作品,至今仍有一种理解中国诚实和深刻力量的感觉。

尾崎秀实在大学时代接触马克思主义以来,形成了社会革命视野下关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做法,大战爆发后,逐步构建了战争引发革命实现亚洲社会主义的理念,从思想到信仰最终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 他关于中国的评论活动集中在1936年到1941年之间,这是中国全民族抵抗运动由于日本的侵略战争而上升的阶段,他聚焦于中国的民族问题,努力与更深刻的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 其中国论述了在表面分裂衰退至极的假死现象的背后,中国民族可以发现抵抗外来征服的主体力量的聚集。 从世界革命理念扩展出来的关于亚洲社会主义的构想也在这个认知过程中产生了。 1942年2月,在回答司法检察官的讯问时,他清楚地谈到了世界共产主义的过渡形态——亚洲社会主义构想。 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将转变为世界共产主义社会。 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苏联一样,这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将诞生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导致世界革命的完成。 由于日本陷入日中持久战争的泥潭,国内社会各方面疲惫不堪,社会革命将会爆发。 此时的日本需要摆脱苏联和资本主义体制的日本和中国共产党完全掌握领导权的支那,这三个民族之间的密切合作。 以这三个民族的密切合作为核心,首先建立东亚各民族的民族共同体。

帝国主义战争引起资本主义内部的混乱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社会革命必将推进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地区社会主义的出现。 这是以古典马克思主义为原点,经过共产主义的国际推进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实践而逐渐形成的社会主义构想,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亚洲主义完全不同。 在尾崎秀实看来,这一理念显然来自对中国民族运动乃至社会革命的持续关注和对社会主义方向的坚定信念。 在1939年出版的《现代支那论》一书的前言中,尾崎秀实深深期待着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是在从数百万中国战场获得切身理解的新一代日本青年回归祖国之后。 这些都印证着战后日本中国研究的辉煌成果,竹内好有野村浩一、藤井升三、丸山升、沟口雄三等为代表。

竹内好( 1910~1977 )在中日战争末期上过中国战场,其艰苦的经历为他后来的中国研究奠定了基础。 战后,他通过考察鲁迅和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构筑了不断快速发展的叙述结构,充分肯定了其内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在鲁迅方面,看到被压迫民族作家的反抗精神,导出了亚洲追求替代现代性的模式。 在中国革命方面,他从辛亥革命到共产党建国,再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现了其历史的内在逻辑性。 这当然是依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因为近代中国的三位伟人孙中山、鲁迅、毛泽东之间看到了这种连续性。 此外,通过文革中反叛的新概念,看到了革命根据地的理论象征意义。 总之,土地革命、根据地与解放区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格局,代替国家完成了抵抗侵略者解放战争的使命。 而且,它也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原型。

这确实是竹内好20世纪60年代反抗日美安保、谋求民族独立的日本构筑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乌托邦,但也有自己的思考语境和外部现实背景。 第一,他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革命人民的世界大潮中,包括民族独立运动在内的中国革命的成功,至少在亚洲取代了明治维新的日本,具有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模范作用。 因为日本的现代化最后走向了殖民地战争,那个民族主义失去了女性。 第二,竹内好激烈反对20世纪60年代来自美国的现代化理论,认为其背后有很强的反共意识形态动机,有理论均质化的倾向。 它也许可以用来说明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但不能说明中国革命的历史。 要说为什么,那是因为中国革命及其现代化是独立于近代西方的另一种现代事物。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竹内好之中国革命论的反西方中心主义性格,以及在亚洲中了解中国,或者被中国认知并波及亚洲地区的做法论的特征。 这和上述尾崎秀实的中国-亚洲论有很大不同的性格。

亚洲中的中国或者中国和亚洲是相互关联的结构。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中国位于亚洲的迅速发展,需要解决与亚洲邻国的关系。 此外,亚洲不是被动的地理经济场,而是拥有多种多样的文化历史和多民族组成的政治领土。 中国需要在亚洲中不断明确自己的位置,而在其活着的变动中的亚洲也在不断地认知和接受中国的快速发展。 这就需要建立能够相互认知相互信息表达的关于亚洲的地区研究体系。 近代东方学/中国学的迅速发展历史,有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足以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思考资源。

本文刊登了《文化纵横》年4月号
赵京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
本文:《“在东西两洋间重述“中国”:近代日本的东洋学/中国学”》
心灵鸡汤:
免责声明:学习兴国网免费收录各个行业的优秀中文网站,提供网站分类目录检索与关键字搜索等服务,本篇文章是在网络上转载的,星空网站目录平台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只为传播网络信息为目的,非商业用途,如有异议请及时联系btr2031@163.com,本站将予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