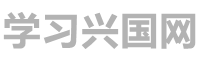“尘肺故事”
/ S2 /相遇了
第一次遇见尔平哥是在双喜村的路边。 和中国其他村庄一样,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双喜村面临着年轻劳动力的流失,逐渐面临着空心化的命运。 就像村民的笑话一样,只有老弱病弱的人才会留在村子里。 尔平哥原本在衡阳住院,这次听说深圳市代表来到导子乡,好不容易冒了生命危险,为了尘肺维权特意回了村。

远远地看,尔平哥,50多岁,1米70几米的身高,灿烂的大眼睛,和普通健康的人没什么两样。 但是,一接近他的身边,就会听到他百米冲刺后沉重的呼吸一样的声音。 一切呼吸仿佛腐蚀着这个身体。 尔平哥在2009年被查出尘肺2期后加了分,但现在已经是尘肺3期,需要整天用吸氧机维持生命。 一位尘肺寡妇的阿姨偷偷对我说:“他可能活不了这一年。” 人到壮年,生命必须突然断绝。

/ S2 /打工
尔平哥喘着气,一句一句慢慢地向我诉说了自己的兼职和生病经历。 1993年,他和村里的几个同乡一起去深圳做风钻工作,属于村里早年外出打工的人们。 20世纪90年代初的深圳只有两条大街。 其中一条是目前高楼林立的深南通大道。 他自豪地说。 “深圳大部分的高楼大厦,我几乎都干过。 他清楚地记得哪座大楼是哪一年建成的,对深圳的地标建筑如数家珍。 国王大厦的项目花了他半年的时间。

当时,尔平哥知道这份工作很辛苦,但收入不高。 在20世纪90年代,一天的工资可以达到60-80元,当时小学老师一个月的工资也是100-200元。 再加上90年代初在深圳开工的工地很少,如果没有亲戚关系的介绍,进入工地找工作不容易,更别说收入高的风穴挖掘工了。 当时的他可以说认为这是一份难得的好工作。 打井需要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在洞里,因为钻头需要用力,所以呼吸会更快。 呼吸期间吸入多处粉尘。 出了洞,每个通风孔匠只有两只眼睛是黑色的,全身布满了白粉。 想想这30到2小时能吸入多少粉尘。 有时,闷热呼吸不畅时,一些工人会摘下那十几天都不换的薄口罩进行工作。

我们不知道。 我以为粉尘一吸入就会被排泄。 不知道会蓄积在肺里。 哥哥没办法说了。 … … 这句话是我在耒阳短短四天没能见到20名工人和患者家属的嘴里,最常听到的话。 90年代,中国还没有推行劳动合同,更别说职业病有什么防护措施了。 大部分建筑工地的工人都是亲戚或家乡关系,一起去城市打工。 办事员之间全靠一封信。 就算是工作一天的钱,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概念。 当时,政府、公司、班级没有告诉他们干风钻的风险。 就像双喜村七八个早期工头死于尘肺病一样,多个带班和工头自己也不知道会引起尘肺病。

疾病。疾病
尔平哥从1993年在深圳做风穴挖掘工作到2002年,2009年被诊断为尘肺二期再加后,不敢做消耗体力的工作。 但是,由于生活所迫,他只能偷偷篡改体检报告,在保安企业做保安,每月给家里一千元的补助金。 直到上了年纪,坐着呼吸都越难受病情恶化,才在家休养。 现在尘肺三期对他来说不仅是个苟延残喘的身体,也是个持续烧钱的无底洞。 妻子为了在广州打工赚钱,自己的生活不能自立,所以和妻子一起住在广州。 但是,广州的医院面临着无法报销的严峻问题。 打点滴一次要200元。 光妻子一个人,全家每月的收入也就3000元。 如果不严重的话,一个月的医疗费需要消耗1000元以上。 如果感冒的话,一个月需要5000-6000元。 去年,尔平哥去北戴河医院洗肺,医药费2万美元。 我查出了这个病,想自杀,不想把房子折断。 他在骂我家人。 比起自己,我认为尔平哥最吃亏的是家人。

维权[/s2/]
这次因为尘肺维权,他决定延期住院,回双喜村等信息。 70多岁的高龄老母亲照顾自己的起居和吃饭。 说起母亲,他真的很内疚,不能作为儿子过晚年,要母亲照顾,白发人送黑发人。
和尔平哥一起进入了他住的黑暗的砖泥房间。 墙上挂着家族照片,房间里陈列着三两件简单朴素的90年代家具。 一进入里屋,床上放着吸氧机,窗前的木桌子上排列着大小药瓶。 哥哥拿出自己从2009年到现在的病例书和肺部ct,仔细地给我们讲述了求医疗的历史,而且也是维权抗争的故事。

尔平哥2009年跟随村里的同乡去深圳维权,当时得到了10万元的赔偿。 但是现在,每个月5000-6000元的医疗费支出,再加上洗肺住院的费用,10万元只是杯水车薪。 年,尔平哥去深圳维权10次,躺在草坪上,睡在马路上,遭遇警察的清场。 尽管感冒病情恶化,他毫不畏惧,一次次地在深圳维权。 这次,更是遥遥回家等待深圳代表给他合理的说法。
本文:《“尘肺故事”》
心灵鸡汤:
免责声明:学习兴国网免费收录各个行业的优秀中文网站,提供网站分类目录检索与关键字搜索等服务,本篇文章是在网络上转载的,星空网站目录平台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只为传播网络信息为目的,非商业用途,如有异议请及时联系btr2031@163.com,本站将予以删除。
下一篇:“新工人艺术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