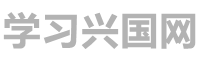“短篇小说:黑美人”
去年春天,我被邀请去看电影。 评论家k坐在我旁边。 电影很无聊,头半个小时,我就盼着它快点结束。 k中途出去了一次,再也没回来。 又过了一会儿,在我们的休息室碰头了。
休息一下吧。 他叫我把烟递给他。
谢谢你。 我不能。 我说。
于是他从里面锁门,点燃香烟,说:“这种东西看盗版光盘就行了。 说是浪费时间”。 躲一会儿去吧。
但是我打算好好看看。 我必须写点什么。
没用,没用! 他摇摇头,你毕业多久了? 从今往后… … 严格来说,这种东西不是艺术,甚至不是电影。
我还没有决定可否。
k带着讥讽的表情说:“不然我们就不坐在这里了,对吧?
但是有些地方还是很感人的。
如果只有感动就行了,艺术就没有价值。 我们说的是艺术,不是吗? 可以感动、哭泣、笑、生气的事件有很多,但那不是艺术。 我觉得这部电影也不感人。 导演对人物塑造一无所知,带来了管弦乐队,部署了军队和警察,建了房子。 他和他的赞助商认为美与浪费的钞票成正比。 他不能理解,有时只有白色… … 够了。 k又点了一支烟,接着说。 否则,哪个经典作家就会失去吸引力。 但是,k摇摇头,说,这是整部电影的第一… … 怎么说呢,泪点多么低俗可笑这句话只是女儿告发了父亲,把他关进大牢而已。 鲍西娅的家人破裂了。 应该流泪吗? 为什么? 有理智的人会这样想的吧。 如果他的父亲是道德败坏的人,伪君子,或者干脆是罪犯,她的行为不正当吗? 从什么是悲剧说起呢?

但是你不害怕亲人反目吗? 我主张最伟大的悲剧常常描写家庭内部的冲突。
但现在不是悲剧的时代! k放声说道。 “我们是希腊人、罗马人,还是莎士比亚时代的人? 任何作者都没有面对过这样冷酷看透一切的观众。 偶尔也看看电视。 目前,各频道都有类似专业节目展览会的家庭内战,无论哪一个泪水、坏话、哀求、阴谋算计、背信弃义,都让《理查德三世》的戏文失色。 但是,小市民们还是那么开心地看着。 一半是为了猎奇,一半是为了遭殃。 所以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没有悲剧了。 即使有也要被当成笑话。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人应该孝顺,这不是最起码的吗? 你怎么能伤害自己的家人呢?
是的,是的! 你应该无条件地接受他们,k打断我的话,不耐烦地说,即使他们的行为卑鄙残忍,也应该学会忍耐和服从。 这就是孝的精神,‘ 国学精华。 我不反对发扬国粹。 但是我不会自己做这个。 我家围墙上有全部二十四孝,我儿子对我说:“‘ 爸爸,这些人在做什么? 你知道我怎么说吗? 我告诉过他,那都是疯子。

我笑了,什么也没说。 k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好像在想心事,沉默了一会儿后,他说。 “我来告诉你这种事。 听着,你能理解我的意思。 这个故事是我朋友提供的。 为了能简单地说明一下,我姑且借用一下他的口气。 但是,请你理解这件事和我或我们认识的人没有关系。

以下是k的描述:
认识我的人不管是从电视上还是从我写的书里都觉得我是独生子女。 其实我有两个哥哥和妹妹。 历史上有很多民族相似的习俗。 从事某种特定职业的人,必须和原来的家庭划清界限,即使像今天这样的过去流传也不会消失。
我哥哥就像我爸爸一样,那种相似的只有基因和后天的刻意臆想、模仿和共同作用才能达成。 如果要拍反映父亲一生的电视剧的话,我哥哥是主角的候选人,即使是最有才能的演员也不像他那样美丽、形象、上帝兼备。 他一直被认为是兄弟中最有前途的一个,事实也是如此,他40岁就坐在老人退休前的位置上。

我哥哥像我妈妈。 他年轻的时候在东北的贫困村庄度过了十年的光景,差点和当地的女性结婚。 从流放地回来,接受教育,同时像一个心地清白的人,他在我们面前总是展现出道德和意志上的优越感。 我说的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正打算和人合作做生意。

下一个是我。 我觉得我不像任何人。 从小到大,我在家里的位置就像寄宿家庭和食客一样。 我哥哥们第一次给妻子看相册的时候,她们隔几页就出现一个陌生的男人,接到指示后才认识到那是我。
我姐姐没成年就去世了。 小妹妹出国留学定居,几乎断绝了关系。
所以经常出入家里的有我们兄弟三人,还有我妻子。
父亲虽然精力充沛可以吃喝,但突然被风吹得半个身体都动不了,不久就再次中风了。
脑溢血的后遗症给他带来了奇怪的恶作剧一样的结果。 他失去了记忆,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所有的历史,也忘记了我们是谁,唯一的认知者是保姆。 总之从漫长的昏迷中醒来后,他成了一个无忧无虑的老单身汉。
每周的家庭聚餐被取消了。 因为老人不让陌生人进屋。 如果他躺在床上,在大厅里听到了什么动静,中风后,他的行动能力下降了,他会变得敏锐,于是,他会挣扎一半,抬起头,恐惧地环顾外面,用老人颤抖的声音喊道。 “过来人啊,过来人啊! 是谋杀

我不知道谁看起来像犯人,从那以后,我们只能趁他睡着的时候悄悄地走到床边看他一眼。 大部分时间,老房子里只有他和保姆两个人。 那几年,报纸上刊登了很多关于独居老人和保姆发生了什么事的信息。 我们不想自己发生同样的事件; 特别是我哥哥,他当时正在审查中。 于是那年中秋节,我们在妈妈的卧室开了家庭会议。

我记得哥哥坐在门旁边的椅子上的时候,蒙着门的哥哥坐在床上。 他们的妻子在窗户里小声说话。 我倚在茶旁边的旧沙发上,伸直了双腿。 妻子搬着小板凳坐在我旁边。
这里曾是我们的活动室,那时也经常这样聚在一起聊天,看书,朗诵文学作品。 这个房间里的一切让我感到亲切和舒适。 20年过去了,陈设品几乎没有变化。 桌子上任何一个小物件的位置都不能说清楚当初是谁,为什么把他们放在那里也仿佛有意无意,有着神圣的仪式意义。 书在书架上排列的顺序也一样。

不知道当初我们在这个房间一起度过了几个晚上。 任何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剧本、诗集,其中平庸的我已经没有印象,美好的东西也只记得片断。 这几年,我经常感到孤独和无为。 每次,都要在脑海里想起一句话,谈谈自慰的事。 就像一个人坐在空的房间里的人,望着墙上的裂缝和图案妄想,消磨时间一样。

我想起负责朗诵的总是哥哥,他也是晚会的第一个组织者。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后来突然离开了这个圈子,和我们疏远了。 那个时候,他想锻炼口才和发音,有一天成为演员。 我总是坐在角落里,一边做白日梦一边偷偷打量着成为妻子的女人。 每当我被小说的情节和爱的幻想所打动,就会跑到墙上的地图前,假装研究地理,掩饰内心的兴奋。 我多次忍住眼泪,暗自想:“生活就是这样吗?” 如果我得不到她的爱,我该去哪里? 后来姐姐去世了,二哥去了,所以我预感到自己的结局也只是死或者出去。 我计划参加游击队死在马来的丛林里; 到了那一天,我想世界上所有诚实的人都会理解我的行为,同时也会给予我爱和敬意的她当然包括在内。

生活总是用意想不到的方法处理哪些不能处理的问题。 如果你认真生活过,就能发现这个秘密。 十几年过去了,我还活着,结婚了; 我们兄弟之间开始在排行榜上互相称呼而不是名字了。 好像是为了特意强调血族关系。
我有理想,有梦想。 其中一个变成了现实,另一个永远坏了。 现在我自觉过着平静的生活,心里没有欲望; 我不想兴奋,也不想后悔。
哥哥依然滔滔不绝地说话。 他把能用10个字可以清楚表达的思想,变成了无聊的演说。 我对他强调的道德、名声、舆论这些词很熟悉。 现实生活让我既明白了那些书面的含义,也明白了实际的用法。 虽说正人君子穿着法衣和鬃毛,但也不会变成别的身体吧。

我突然感兴趣,打断了他的话,说:“你在说什么名声啊。 老人都这样了。 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 谁能影响他的名声呢? 人活着是为了名声吗?
那人为什么而活呢? 哥哥朝着我,有点生气,问道。
为了吃! 哥哥急忙说。
放声大笑了。
我想是钱。 我说,你那是低级的。 什么是实现自己? 就是发财。 到时我带你们发财。 怎么样?
好吃的喝辣的!
一起去! 一起去!
没错! 一起去吧!
还有姑娘们。 哥哥补充道。
这个白字清晰引起了我的喝彩。
女人们停止对话,皱着眉头看着我们。 就像看着那些玩愚蠢游戏的孩子们一样。
小声点吧。 老板说。
大家都沉默了。
我笑着走到地图前面,显得漫不经心。 二十年过去了,一点国家消失了,一点国家诞生了,地名变了,边界变了。 但是,这张地图和当时一模一样。 据说雨林很快就会消失… … 游击队怎么样? 还有豹子、老虎和貘。

不知道为什么,我轻轻地哼着《小芳》的曲调。 那个时候,我脑海里总是这首歌。
那时,我妻子悄悄地从后面过来,用只有夫妻之间才能察觉的秘密方法做了警告的手势,然后把目光转向了二哥。
我不知道那个老好人对什么感到不快,但是作为让步,我出去抽烟了。
从厨房回来的时候,头脑不太清楚,走错了门。 老人这时已经醒了,躺在床上喝水。 我吓了一跳,匆匆回到昏暗的走廊。 那时,我看着他昏昏欲睡,平静的男中音说:“你在找谁?
有一瞬间,我以为他认出了我,但很快他又问:“你在找谁?
这时保姆来了,问我是不是把暖气修好了,把我领到了房间里。 这个女人的智慧和品格都比我们想象的好。
老头子很高兴,从床上爬起来,看到我在工作。
我一边装腔作势地检查管道,一边和他聊天,停留了约10分钟,很有礼貌地失礼了。 回到另一个房间,我把这次奇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
那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漱口,舒服地躺在床上,准备睡前读几页书。
妻子坐在梳妆台前。
突然她说。 “你可以晚点再去见你爸爸吗?
怎么了? 我坐起来,问。
没关系。
我是说,她说。 开始呜咽。 爸爸真可怜啊。 他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必须帮助他。 可以吗?
我跳下床,赤脚走了两步,站在卧室的中间。
可以吗? 她转过身来,含着眼泪问。
当然,我… … 我也是… … 请放心。 我抱住她的头,轻轻地在她的背上拍了一下,说。
下星期天,我又去了老人那里。 他说带着空来玩,可我是受到这样邀请的难得的水暖工。 我在沙发上坐了15分钟,喝了一杯茶。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周都去看他。
老人行动不便,也不喜欢电视。 醒来时唯一的兴趣是读自己的藏书。 从《李自成》到《乔厂长就职记》,从《金陵春梦》到《青苹果外传》,还有几部诗选。 总之机关图书室里一定有什么书?
每次见面,他都会和我说最近读了什么书、读了多少、有什么精彩之处。 那样兴奋和快活的样子,足以证明他以前从没翻过这些书。
当时是20世纪末,对于文学作品,他的态度和拉曼查乡下的神甫一样严厉。 小说总是很危险的东西。 一本好小说会引起网民想当作家的想法,什么样的坏小说有助于他们建立信心。 很多原本能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才都被这样无聊的文案生涯所引导。

同样的事件也发生在我父亲身上。 他已经80岁了,半身瘫痪,连笔都拿不动,一辈子除了公文和私人文件什么也没写,却摆出一副文人的样子。 最可笑的是他认为自己是有名的作家,或者文艺评论家,最起码是诗人。 他指着《广场诗抄》里的几篇,声称那是他写的。

对他这样的自我定位,我一方面感到荒谬,另一方面也觉得可以利用。 有次闲聊的时候,我说自己在上夜校,想参加大人的高考,委婉地请求他为我辅导功课。 老人很爽快地同意了。 我们约好了每周上一次课。 这样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出入他家了。

春天在他的指导下复习学习。 星期天早上9点,我走进了那个书房和卧室。 老人总是笑眯眯地指着床边的沙发说:“来了吗? 好的,请坐。 之后,打开教材用的中文教科书,开始进行说明。
我们上了半个小时课,休息一下,聊聊天,看电视。 途中保姆最近两次等着喝水和吃药。
我是个勤奋的好学生,很受老人的欢迎。 他觉得像我这样时代的青年帮我修暖气很不甘心。 总是抱怨我和知识改变命运,不让岁月浇水等等,为了表示重宝,让我一起吃了午饭。
到了夏天,他的健康明显好转,能够一口气读完单元的课文,我们的友谊也更加深厚了。 我把自己的妻子和哥哥们介绍给他。 国庆节的时候,我们一起庆祝他的生日是我和保姆共同决定的。 家人终于又团聚了。 我们笑着唱着喝着,围着爸爸,不停地碰杯,擦眼泪,各自紧紧地拥抱着他。 在酒店走廊里,哥哥不得不拉着我说心里话。 我们都喝多了,互相扶持,贴着头,把酒味喷在对方脸上。 在愉快的嘈杂声中,我只听到他多次呼唤我。 老三、老三… …

这次聚会后,因为女儿病了,所以我两个星期没去老人家了。 到那天为止是11月… … 我走进大厅,跺着脚脱下大衣。 保姆笑着来接我。
三哥回来了,她说,你去看看,爷爷在写字。
我很意外,很高兴,跑过走廊,掀起几个卧室门帘向里面看。 我看到了一位老人,他倚在床头,盖着薄被子,拿着沾在竹管上的钢笔,在稿纸堆上涂着什么。 他严肃的样子、严肃的表情,让人联想到病中的涅克拉索夫。
我拉开门帘走了进去,说:“你好,写了什么吗?
老人看到我很高兴,扔掉纸和笔,命令保姆烧水泡茶。 我们闲聊了一会儿之后,又开始上课了。
他发现我有一定的文学鉴赏力后,将我提拔为知己和私设秘书的职位,经常在我面前发表关于文学、历史和哲学的见解,同时我也期待着我能像埃克曼一样成为忠实的记录者,有一天这些宝贵的思想会出版并公之于世
果然,在上课的间隙,老人主动给我看了稿纸。
请看一下。 我还在编造,手不好使。 他笑着说。
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三字经一样的韵文。 文案没什么新鲜的,只是在几千年来唱的老调里灌了一些时髦但不一定恰当的词。 我感兴趣的不是复印件,而是钢笔本身。 我想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用同样的笔体写的东西,但是一时想不起来写的是什么。 我正在努力回忆,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于是老人回来了。 他在保姆的支持下,毫不费力地移动到床边。
这是你写的吗? 用左手写的!
他觑了一下眼睛,马上就有点腼腆地说。 “啊,这是报纸的征文。 街道让老同志参加。 我用那个练习写字。 我写得像爬蜘蛛网一样。
的… … 这是你写的吗? 真的吗? 是什么时候写的? 刚才… …
我迅速地从头到尾浏览了一下这篇草稿。 我抬起头,全身在发抖。
这怎么可能呢,这个字… …
我绝望地面对保姆说:“这是爷爷写的吗? 看到了吗? 你亲眼目睹了!
我没等她的回答就跑出了房间。
我回到自己家,一进门就开始翻箱子,倒箱子,最终在床下的旧箱子底部找到了东西。 那是信封自制,带水,上面字模糊的信。 我拿出信纸,平整地摊在地上,把从老人那里拿来的稿纸铺在旁边。
我蹲在地上对着这两张纸,过了一会儿,又跪下看了看。 最后趴在地上,皱起鼻子,一个字一个字,仔细地盯着每一笔,试图从细节中找出什么。 我想如果我是审判员,诚实健全有充分的理性的话,面对这样的物证,会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我的评价决定某人的生与死。 就像现在作为证据的这些文件曾经决定了另一个人的生与死一样。 我下午坐在地板上,我想我不能下结论。

那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和家人一起吃饭,聊天,看电视。 她们安静下来之后,我轻轻地爬起来走进书房,遮住门,打开台灯。 我用钢笔把重复出现的字圈了起来。 那些如下所示。
尊敬的会员让我冒了重大的生命我的总长忠礼是西藏分子地主级的孝子贤孙时,做着天翻地复的梦死也不改他的祖父化文,和港台的私营工农大众极其一样
然后,把两张纸重叠起来,打开灯,让这些字依次重叠。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奇迹会发生。 我想在这个证据中找到一些破绽。 因为即使是只有最熟练的律师才能使用的暧昧混淆,也有理由为了推翻那个可怕的结论而做出象征性的努力。 就像赌徒翻遍口袋发现了小钱一样,还能说“我还有机会”。

但是,我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两种笔迹几乎都像复写纸誊写的一样。
我痛苦地叹了口气,把头伏在桌子上。
就在那时,书房的门开了,妻子出现在门口。 她穿着睡衣,头发披散,脸上带着睡意。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 她用奇怪的语调问道:“你在做什么?
没事… … 写点什么。
写什么呢,鬼鬼祟祟的。 我看看。 她说她是冲着桌子来的。
我想站起来阻止她。 但是,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没有权利对她隐瞒这件事。 20年前,她的家人被无情地毁灭了,但现在这个血腥事件的最后疑问终于解开了。 我应该把证据放在她面前,让她自己去看,自己评价。

我问你一件事,我说,你还不记得了,多年前,我,我父亲,给你… …
我停下来,看了看她的眼睛。 她也注视着我。 她的表情渐渐严肃起来,在我看来,她眼中的爱和温暖也似乎消失了一点,落日沉入大海后,玫瑰色的晚霞似乎在淤血般的黑暗中慢慢消失。
我没有资格继续爱他,崇拜她,和她一起生活。 你觉得接下来我还剩下什么? 我凭什么活下去?
那时,女儿醒了,在卧室里大声叫她,声音很高,声音很急。
啊,老实说,妈妈来了。 她尖叫着,匆匆地出去了。
我急忙把那两张纸锁在抽屉里。
第二天,我又跑去找老人了。 他情绪很高,好像忘了我前一天的奇怪行为。 我们坐在一起看电视。
我再看一遍那份草稿。把拿去的那一页夹在中间,放回他的床头。
对不起,请换一下频道。 老人放下报纸,说。
您要看哪辆?
该死的家伙。 他说他一辈子九老了,喜欢看九频道。 就是这条命。
啊,臭九看九频道。 他反复说,为这俏皮话感到自豪。
我和他都笑了。
你不认识一个叫什么忠礼的人吗? 过了一会儿,我问。
他和你是同事,他妻子叫江鹏。 他们有个小女儿。 如果活到现在应该和我一样大。 有印象吗? 他们家住在这附近,大概是30年前的事了。
我一边说,一边注意他的反应。 我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如何从表情和动作来评价身体是否在说谎。 在我看来,他是个好骗子吗,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的女儿和小时候是伙伴,一起玩。 这几年我一直在想她。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再见她一次。 他们全家都是好人。 请回想一下。 关于这个身体,他现在在哪里?
父亲仔细听了我的话,郑重地回答了。 “我会好好想想的。 何忠礼… … 记住。
我看见他拿起笔,在报纸的边缘一笔一笔地写了那三个字。
接下来是沉默。
到了该告辞的时间了,我还坐在沙发上。 我默默地环视这个房间,回顾在这里度过的岁月,想对他再说几句话。 因为我预感到自己不会再回来了。
突然看到了书架上的艺术品。 那是乌木黑人少女的头像。 她圆润的头骨、饱满的嘴唇、富有原始艺术风味的头饰和项链,曾多次将我带入不可思议的幻想世界。
我想再听一次老人关于这座雕像的由来的故事。 在那个故事里,有蓝色波涛汹涌的海湾,白色的海岸炮台,像烤面包一样裂开的黑色非洲群山,有很多我一直珍藏在心底的影像。 翡翠色平静宽阔的河流一下子坠入万丈深渊,从彩虹复盖天空的雾中升起,又消失了一半。 豹子在车旁奔跑,敏锐地越过了灌木丛。 树干的树枝摩擦着他的皮毛发出轻微的折断声… …

故事的主角是老人的另一个同事,他去了非洲,同时死在那里。
故事结束多年后,人们终于想起了吊死他。 发现那块白石头堆起来的坟墓比最初高了近两倍。 然后,星期一到混凝土柱子竖立的地平线,开着淡紫色的小花。
还记得这句话的意思吗? 我指着雕像底部的斯瓦希里语小组,问道。
这个还不太清楚,我想是不是商标。
是商标吗?
是的,有可能。 老人说。 啊,是的。 英语怎么样?
我英语不好。
他似乎为我感到惋惜,说:“应该好好学习英语。 英语第一是国际音标,记住音标的话就可以自学了吧。 ”。 我为了学习英语,在电视上看到了背词典,一个个背单词的年轻人。
我也背了下来。 我背到了f。 我说。
那时保姆进来宣布吃饭,我趁机失陪了。 出门前,我静静凝视着那尊美丽的雕像,送亲。
之后不到一个月,老人毫无征兆地去世了。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工作,一直握着最喜欢的笔杆。
在他的追悼会上,我们站成一排。 我妻子和女儿站在我旁边。 她对女儿说。 “好孩子,亲吻爷爷,看看爷爷。
女儿犹豫地走了两步,被我从后面拉着肩膀回来。
怎么了,怎么了? 她惊讶地看着我,挥动着我的手臂,喊道。
我想,这个女人,她有权知道哪个事件,但她永远不会知道。 这是多么可怕,多么可怕!
k微笑着向我点头,表示他的话说完了。
那几门外语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问。
k叹了口气回答说。 “我不知道。 那个朋友没有告诉我。
他,是你的朋友,现在怎么样了? 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也有那封信。 那是什么样的信?
我想那是告密书。 k认真地说,马上点了点头。 当时,这样的事件经常发生。
即,… …
k笑着挥手,表示对我的推测不作任何回答。
接下来是沉默。
过了一会儿,服务员进来了,我们出去了。
本文:《“短篇小说:黑美人”》
心灵鸡汤:
免责声明:学习兴国网免费收录各个行业的优秀中文网站,提供网站分类目录检索与关键字搜索等服务,本篇文章是在网络上转载的,星空网站目录平台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只为传播网络信息为目的,非商业用途,如有异议请及时联系btr2031@163.com,本站将予以删除。
上一篇:“二元问题之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