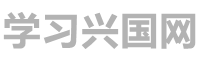“刘复生:另类的宗教写作张承志宗教写作的意义”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张承志的宗教创作极为另类。 虽然它采取宗教文章的形式,但并不是指精神、神圣性或唯灵的热情,相反,它没有离开世俗世界和时代的命题,表现出现实的批判性、抗争性,因此张承志的宗教文章中充满了异端的气质和对体制的对抗色。 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大转折中(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他经由伊斯兰教异端派哲合忍耶,找到了表现全球化背景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人民生存状况和命运的立场。 在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世界秩序中,张承志以民族和身份为基点,获得了批判的边缘位置。 在任何体制内,只要这个人制具有压迫性,他就是其中的少数。 永远和弱者、受压迫和剥夺者站在一起。

本文原刊于《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3期,感谢作者刘复生教授、公众号海社科授权发表。
另类的宗教创作:张承志宗教创作的意义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指南》中,马克思说,宗教中的苦难是现实苦难的表现,也是对其现实苦难的抗议。 宗教仿佛是被压迫的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没有精神制度的精神。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1]据此,马克思经过对神学的批判进入了对法的批判和对政治的批判。 但是,马克思这个19世纪对德国宗教的批判,在中国作家张承志的宗教书中是无效的,也是相反的。 宗教确实有现实的苦难起源,是对它的抗议,但不是人民的鸦片。 相反,它是对各种世俗形态的鸦片[ 阿q精神和犬儒主义人生哲学]的反驳。

这并不意味着张承志的宗教创作确立了与现实世界不同的精神维度,或者说是乌托邦,形成了不完整的现实和批判的张力。 当然,他不能单纯从与理想主义、人文精神等相似而非的描写中得到恰当的解读。 实际上,张承志也从未像通常的宗教书籍那样沉浸在彼岸世界的写作中。 (如果说写他的宗教书前期——《九座宫殿》、《残月》、《黄泥小屋》的时期,这种气质还不明朗的话,后面的《西省暗杀考》、《海骚》、《心史》异常确定) )。 所以,在张承志的所谓宗教小说中,对现世的厌倦、淡漠是永恒的,对生活的苦难没有超脱、冥想、超越的思念,不是彼岸对世界的皈依、救赎等主题,而是对现世不断抗争、介入的热情。 正如《西省暗杀考》、《心灵史》等作品所示,现实的苦难绝不是升入天堂的阶梯,而是异端存在的理由。 由此可见,张承志的宗教创作中充满了异端的气质和对体制的对抗色彩。 所谓牺牲之美,就是抛弃西德(复数形式为束海达依,也就是伊斯兰教的牺牲),圣战,在宗教意义上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因为,它们要捍卫的不是宗教的神圣,而是被压迫者的心灵自由和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利,以及不公正、不义的体制权力,张承志在《心灵的历史》中说异端就是美——这是人类的法则。 所以,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宗教不过是张承志的批判战略,他获得了对时代和现实批判性的替代立足点。 这并不怀疑张承志的宗教信仰的诚实,相反,正是诚实才使这种批评具有了情感的深厚和文学表达的力量。

因此,对于作为作家的张承志而非作为信徒的张承志而言,张承志的宗教创作并不是指精神、神圣性或唯灵的热情,相反,它虽然采取的是宗教创作的形式,但从未瞬间离开世俗世界和时代的命题。 从本质上看,张承志的宗教创作具有强烈的世俗性,充满世俗关怀和具体而宏大的政治需要。

异端的角度和现实的批判性、抗争性使张承志的宗教创作极为另类。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许多作家向文学注入了宗教意义表达,形成了清晰的创作语境。 在现代文学中,许地山、丰子恺、俞平伯、废名、惊蛰等的创作都有浓厚或浓厚的佛教色彩,冰心、老舍、萧干、林语堂等的创作中也蕴含着不同程度的基督教气质,这一点广为人知。 这些作家的宗教创作和他们所处的历史语境有某种潜在的联系,但宗教对这些作家的文学来说首先是生命个人人生体验的表现,或者说是对超越人生兴趣的追求,是儒家文化出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确立人生意义的新精神选择,或者是 [2]因此,对这些作家来说,宗教的意义是文学的或审美的。 宗教为他们的创作增添了深厚的藉美学风格、理想性和浪漫主义情调。 因此,除了许地山等极少数是真正的信徒,在某些创作中用信仰来解释人生之外,大多数作家实际上并不是用信仰来写的,最多只是吸取了某些宗教的义理和情趣。 典型的如周作人俞平伯《古槐梦遇》中所说,必须要成为僧侣,但真正不能成为僧侣,可以说是打破了这个奥秘。 同样,周作人在《圣经与中国文学》中盛赞《圣经》,预言它将对中国文学产生巨大的影响。 所有的理由都是具有高度文学性的美文。

在现代文学中,情况不同,20世纪50年代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事实上取消了宗教的合法性,宗教创作的线索几乎消失了。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些理想性很高的革命文学事实上具备了宗教性。 [3]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即改革开放的时代,新启蒙主义成为主导意识形态,是以人性、人道主义对抗、反思神圣性的政治理想主义,宣传个人世俗欲望的合理性,成为主流趋势。 由于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的理想品格,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仍然是理想的文学,但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显然改变了他们在革命年代教育下形成的理想主义。 这种理想主义形式嵌入了新的复制品中,政治复制品被取消、改变,变成了单纯地追求个人人生的意义和生存价值。 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家热衷于探索人性,思考生命的深度和意义。 因此,关注存在主义、精神解体等生存意义、心灵多元性、多样性的现代主义观念成为影响文学思潮的主要哲学话语,是有道理的。

但是,新启蒙主义启蒙的世俗化社会和市场化时代,导致了欲望的泛滥和精神的低俗化(这个过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所谓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就是其历史反映)。 。 在这样的背景下,宗教文章显得沉重而备受关注。 20世纪90年代,热衷于形式探索的先锋作家北村皈依了基督教,写了宗教信仰很强的《洗礼之河》等小说。 “愤怒”也是如此,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病隙杂笔》等信仰背景尚不确定,但从对命运和苦难的想法来看,这一时期的宗教书籍也有突出的特征,大大强调了信仰的意义,世俗与信仰之间。 史铁生、北村这样的作家对人生苦难的体验有极其个人的原因,但不可否认,世俗化、堕落的社会、时代环境构成了他们潜在的对话对象和对抗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次信仰维度的作家、批评家多皈依基督教(或将其作为精神资源),如北村、刘小枫);史铁生即使没有基督教背景,也从中吸取了许多资源) 对提高佛的出世、道路的世俗性、文化的人气很好,世俗商品和伊斯兰教在通常的误解中,似乎是太极端的宗教,不过是极端主义而已。 这也是所谓爱好自由的知识分子所害怕的。 另外,或许,从启蒙主义的观点来看,基督教更具有普遍性、精神超越性,具有主流的文明气质,因此也符合追求精神高贵和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喜好。 基督教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似乎具有对抗世俗精英主义的象征性。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张承志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和文学表现,以及伊斯兰教中的一个中国化的神秘主义教派哲合忍耶,其含义完全不同。 但是,由于《心灵史》在20世纪90年代初也出现了,因此由于其宗教性,理想主义明显被广泛误读——张承志被认为是以宗教和理想主义对抗世俗、商品主义和普遍精神落魄的作家,与其他宗教书籍混淆了。

张承志对哲忍耶的信仰及其文学表现,是二十世纪宗教创作乃至中国文学中不折不扣的另类。 他以哲合忍耶为中心的小说创作,并不是为了增添文学中的美学风格、色彩,相反,他通过这样的创作废除了文学。 (虽然心的历史具有超越文体的含混不清之处,但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小说、文学。 )心灵历史之后,他放弃了古典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只写非虚构的随笔、杂文。 另外,他高举信仰旗帜也不仅仅是为了对抗市场社会精神的堕落——巧取豪夺的人把他和张炜齐名,称为二枚,投降(向市场、世俗投降)? 人文精神的代表,显然是张冠李戴(张炜名副其实),也是对其清洁精神的误读。 不如说,他在宗教创作中挑战的对象之一是精英主义的人文精神。 《心灵史》等作品表明,他与所谓的知识分子——他称为智慧阶级,是公然对立的。 张承志想要宣传的是带有某种民粹主义色彩的人道1980年代以来流行的知识分子关于人道主义和对立的人类的观念。 通过哲忍耶,他找到了对抗体制(包括与体制共谋的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不折不扣的异端位置。 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大转折(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中,他找到了全球化背景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中国的情况以及人民在这种情况下的生存状况和命运的立场。 由此,受到压迫和剥夺的)经济、政治、表达权的)哲合忍耶,成为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或不公正、不自由的世界秩序中的人民的隐喻。 而哲合忍耶的反抗和牺牲,成为了他倾心、渴望的反体系革命力量的象征形式。

张承志真正在小说中意识到宗教性并开始刻意强调是从1980年后半期开始的,1990年代初的《心灵的历史》达到了顶点。 同时,他选择了非常异端的哲合忍耶——事实上,正因为他发现了革命叛逆的哲合忍耶,才决定用文学的形式来表现宗教,并不相反。 正因为信仰伊斯兰教,才决定表现哲合忍耶。 如果不是张承志进入西北,遇见哲合忍耶,基于血缘的伊斯兰信仰未必能为张承志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提供根本的方法,也无法对文学生涯产生根本的影响。 哲忍耶让张承志重新认识并真正找到了对伊斯兰教信仰的最终根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承志把自己与哲合忍耶的相遇说成是某种预定,哲合忍耶让他认识了,但张承志本人的自传中充满了命运神秘色彩的哲合忍耶 必须指出,实际上有着坚实的世俗或社会原因,它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和他的个人经历直接相关。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包括张承志在内的被知识分子追求的现代性开始岌岌可危,改革开放、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追求现代性的快速发展道路已经显示出了其代价,或者开始出现了其征兆。 下层民众,是承受着迅速发展代价的广大群体成为弱者和不能呐喊的社会群体,而上层民众在新的社会秩序中的财富、社会机会和表现空之间的垄断。 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成为了不容忽视的残酷现实,被批判的知识分子感知并意识到。 这使得张承志和中国当代主流知识分子(事实上成了新体制的同谋)脱离了思想。 随着远离主流知识界,他终于退出了合作社,成为了彻底的异类。 一贯怀有民粹主义倾向和底层情怀的张承志不能认同民众在现代化社会秩序中的普遍命运。 张承志的宗教创作与他初次登上文坛时为人民而创作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为此,张承志在《心灵的历史》序言中说,我在1978年因童言而悔恨的口号——被嘲笑了‘ 为了人民三个字,我已经可以说对了。 我在全美做了那个。 这是对你们的制约; 现在我履行了诺言,没有失去信誉。

此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张承志访问了美国、加拿大、德国、蒙古等国,特别是他在日本的逗留经历,使他认识到全球化时代被称为中心和边缘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和文化秩序,清楚认同自己的文化认同,在张承志的视野下, 因此,将张承志的反美、反日角度等同于所谓民族主义角度[4]并不容易,在张承志的词典中,美、日多为后殖民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代称。 张承志有国际主义的视野,在他那里,民族差异只有与阶级(或权力的中心和边缘)和政治不平等(或政治文化压迫)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 在小说《金牧场》中,张承志一方面批判作为资本主义中心国的日本,另一方面将日本内部正直、富有抗争精神的平田英男和真弓区分开来,特别提到了对抗体制的左派学生运动的全共斗。 [5]因此,解读张承志的宗教文章不能离开这个前提。 在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世界秩序中,他以民族和身份为基点,获得了批判的边缘位置。 他的第三世界的角度是功能性的,无法进行本质的理解,所以他在对抗以日、美为代表或象征的世界权力体制时,强调了自己的中华民族身份,但在中华民族内部却借用回族和哲合忍耶宗派强调了少数民族的异端位置和中华内部的第三世界身份。 在《心史》中,张承志说我批判了偏狭、狭隘的民族主义。 其实,不管什么体制,只要这个人制具有压迫性,他就是其中少数。 永远和弱者、受压迫和剥夺者站在一起。 在哲忍耶的帮助下,张承志一方面批判了绞杀内心自由,捍卫既得权益和压迫结构的不公正的权力体制,批判了中华文化的中庸之道和犬儒主义的人生哲学。 因为容忍了这种民族性格不合理的体制。 张承志所赞扬的血性、牺牲不仅是理想主义,也是革命精神,是对现存一切不合理、反人道社会秩序的反抗精神,由此,宗教与张承志一贯的左派精神在深层联系在一起。 可见张承志的宗教创作和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和国家共谋)之间相当紧张甚至对抗。 这也可能是着名作家张承志的《心灵历史》找不到杂志发表,只出单行本和收入文集的原因。

在写完《心灵史》后的写作阶段,张承志放弃了小说的写作,基本上也放弃了宗教的写作。 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写作。 更批判地、更直接地走向历史和现实,写了许多散文、随笔、杂文,他走向了他衷心喜爱的鲁迅之路。 如果说他的宗教创作披着神圣的衣服批判时代和现实,那这个时候他干脆放下宗教的包袱直接介入时代。 从这里似乎也可以追溯出宗教对他写作的意义。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本论文不认为儒家文化是所谓的儒教,也就是宗教文化。 当然,佛和道事实上很久以前就传达了士人补充的精神资源。 因此,谈论佛的论道,也可以说是现代知识分子在以前流传下来的边境地区和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寻找精神资源。 当然,佛和道在现代的意义完全改变了。

[3]黄子平曾经指出,许多革命历史小说暗中利用或借用了许多宗教隐喻。 黄子平《革命·; 历史&混合; 《小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或《灰烬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4]关于张承志的反美、反日或更确切地说是反西方的观点,请参阅散文《打破你的签证回家》、《日本的信息》、《无援的思想》等。 其实,这个反西方的角度也是对西方现代观念,特别是持有这种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

[5]《金牧场》在张承志的创作生活中具有转折性的重要作用。 这部小说留下了他自己内心的挣扎、矛盾和困惑。 他后来的一些思想在这部小说中已经开始形成,但还不够清晰,还很混乱,太感性和表象了。 其实,这也许也是他采取了相当现代主义形式,不得已的理由。 但是,这部小说中的思维在当时已经相当超前了。 当然,因为这样的进步必然引起的粗糙,他对这部作品最不满。 他后来重写了《金牧场》,改名为《金草原》。
心灵鸡汤:
免责声明:学习兴国网免费收录各个行业的优秀中文网站,提供网站分类目录检索与关键字搜索等服务,本篇文章是在网络上转载的,星空网站目录平台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只为传播网络信息为目的,非商业用途,如有异议请及时联系btr2031@163.com,本站将予以删除。
上一篇:“人类文化的三个原点”
下一篇:“中国三大宗教的哲学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