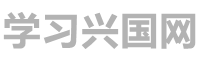“文化革命”视野中的“延安文艺””
如果把延安时代的政治革命放在现代的范围内理解,即理解为现代语言的实践活动,那么歌剧《白毛女》中所看到的政治革命其实也只是文化革命,或文化革命的一种表现。 在詹姆逊的理论中,任何艺术都代表着意识形态的需要。 相反,任何意识形态都必然包含着艺术的方法隐喻、象征、乌托邦。 这是因为可以说意识形态是乌托邦,乌托邦是意识形态。

在拆除延安文艺的复制品中,唐小兵实现了延安文艺,也就是充分实现了‘ 大众文艺实际上是一场猛烈的文化革命运动,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悠久的乌托邦冲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歌剧《白毛女》相当完美地突出了延安文艺所具有的文化革命的意义。 因此,我们需要并必须把握延安文艺所蕴含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价值,即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乌托邦的想象。 它一方面是现代政治方法对人类精细行为、艺术活动的‘ 功利主义的重视和利用,一方面代表着人类艺术活动本身所蕴涵的最深刻、最原始的欲望和冲动直接实现了意义,生活充分艺术化。 从这个角度看,延安文艺是一场包含深刻现代意义的文化革命。

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往往依赖于新意识形态的推进。 在这些决策中,构建意识形态认同已成为进入延安时代的共产党的主要任务。 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几乎都属于偏远的山区和农村,本来就处于长期的经济文化落后状态,比平原和沿海落后了几十年甚至一百年。 这些地区占统治地位以前流传的意识形态显然不利于新政治授权的建立。 农民承认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力就像承认能够控制局面的武力一样,但他们显然对这些武力缺乏心理和文化上的认识。 他们也对近代道德的衰退感到不满,但对只追求利益、不道德行为带来的灾难往往束手无策。 他们一如既往地指责和嘲笑富人,但骨子里依然充满着对富人生活的向往。 因此,要确立新政的合法性,不仅要依靠武力的比较有效性,要迅速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还必须在农民心中灌输新的认可理念。 这个理念必须通情达理,当然不是用武力树立,而是要依靠文化、艺术、审美的力量。 因为正如詹姆逊指出的那样,道德状况只能从审美状态迅速发展,而不能从物质状态迅速发展。 另外,正如席勒把艺术看作深入人类主体间性的中介形式一样,人们在经验中需要处理的政治问题中需要伪道美学问题。 那是因为只有通过美女们才能走向自由。

与其他艺术类型相比,作为集体艺术的戏剧无疑是最适合表达这种政治美学使命的艺术类型。 以构筑共同的文化·心理构造、共同的价值观·形态、共同的情绪、共同的焦急和憧憬为目标的时代,大多是戏剧繁荣的时代。 每当意识形态感受到集体本质认可的必要性和紧迫感,重温或再现想象中的共同体,戏剧就具备繁荣的客观条件。 在剧场里,悬挂着现实个性的观众,真诚地感动着投入到共同的感情世界里,集体精神占领着个人的心,人们在剧场里过着共同的生活。 这个优点经常使戏剧成为民众的狂欢节。 中国戏曲迅速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戏曲与原始祭祀仪式、民间节日有着很深的渊源。 近代以前的中国人交通不便,居住分散,仅靠戏曲不容易吸引大量观众。 正是万民同庆的民间节日帮助戏曲克服了这个巨大的困难。 戏曲依赖节日,节日伴随戏曲。 中国的民间节日大多是全民性的,这些举国上下的人们痴迷的民间传说中的节日,带来了节日观剧时的贤愚毕至、男女老少咸集、万人空巷的盛况。 正是因为戏剧具有这种其他艺术形式所没有的功能,在构建政治认同成为延安文艺的基本目标之后,延安大众文艺,不仅要克服通俗文学的客体化成分,更要摒弃现代主义的个人化政治。 这个大众文艺的具体形式包括‘ 从长篇体裁、多而杂的性格心理描写、琐碎的故事描写等(周扬语)开始强调戏剧、曲艺、民间文艺以及带有狂欢色彩的集体欢庆活动。

准确地说,延安文艺选择了戏曲而不是戏剧。 从前传到中国的戏曲从兴盛之日起在用歌舞演故事(王国维语)以前就传了下来。 正统的意识形态观念从演绎正史的空隙中,将忠臣义士、义夫节妇、孝子贤孙的故事渗透到了老百姓的心中。 戏剧服装、道具、节目营造出的强烈的仪式气氛等,戏曲特有的仪式性,让观众感受到上下尊卑的秩序,受到以前流传下来的礼仪魅力。 由于戏曲受到农民的喜爱,其渗透力和感染力是其他途径无法比拟的。 对古代戏曲艺术家和批评家来说,戏曲的首要功能是道德教化。 用汤普森的话来说,能迎合君臣之节,能沐浴父子之恩,能加深幼儿之睦,能打动夫妻之喜,能献宾友之礼,雪恨之结,已经是令人担忧的疾病 … … 人有这个声音,家有这条路,不检疫,天下太平。 不是人情的大洞,而是名教的至乐哉! 虽然戏剧的政治功能明显,但剧中的政治是审美政治。 中国古代戏曲是音乐(艺术)的一部分,是情感的经验形式。 政治道德化不能合情合理。 《毛诗序》从如何将人类的各种感情纳入道德规范中而不是胡乱泛滥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表露感情、停止礼义的观点,从而通晓了《乐记》的所谓乐师、伦理 戏剧之所以成为延安时期和文革时期最重要的艺术类型,显然与这种独特形式的意识形态功能有关。

抗战期间,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大规模的城市向农村的文化转移,许多城市知识青年随八路军和新四军来到乡村,为面向农民的大规模推进民族主义提供了条件。 他们创作了多部小说、诗、剧,表演了俄罗斯和苏联的大型戏剧,举办了大型文艺比赛,公演时观众也很多,但还是老百姓只是在看热闹,真的不能理解。 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这一切。 认为《演说》从理论上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必须先普及再提高,确定文化革命的寻求途径必须首先是农民可以接受的途径,主张利用农村各种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轻松教学。 《演说》之后,民谣、地方戏、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民间文艺形式逐渐引起知识分子作家的重视,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进入农民的生活,很快摆脱了阳春白雪式的说教方法,与民间艺人结合,开辟了戏曲生活的新天地。 陕北地区的秦阀、信天游、郿鄠戏、道情、秧歌、花鼓等都是文化革命的形式。

一位从国统区初到鲁艺的剧作家,就自己对鲁艺的看法这样说道。
到延安鲁艺时,鲁艺大部分去乡下演出了。 回来的时候,在鲁艺大门外的空地上做了地基,立了几根木棍,与天幕立了两个大幕开始演戏。 观众坐在地上或站在小土坡上观看。 连续三天,节目有《兄妹开荒》、《二流子变英雄》、《周子山》等,有乐队伴奏,演员扭扭秧歌,说陕北方言,打扮成陕北的农民、干部、民兵。 没见过在戏里演的… … 我看的是新剧… …

1943年,在周扬的直接指导和张庚、吕骥的统一下,鲁艺全院的师生几乎都参加了秧歌的创作和排练。 黄钢在一篇文案中描述了鲁艺秧歌队(当初被称为鲁艺推进队)的巨大政治作用。
从剧场到广场,这种演出场所的变化标志着延安戏剧活动发生的巨大变化。 川口区的一位女性在看鲁艺推进队的公演时说:“以前不擅长鲁艺的戏,但这次明白了。 许多节目中的曲调为农民所熟知。 东乡罗家坪公演的时候,《推军花鼓》的王大化,李波唱猪羊,会去哪里? 当时,老乡们马上继续唱着“给那个勇敢的八路军”。

戏剧在整个延安时期的重要性不亚于文革时期。 整个延安时期,戏剧的狂欢、仪式和叙事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戏剧在这种艰难的生活和斗争中的繁荣显示了戏剧不可替代的意识形态功能。 这样组织起来的戏剧活动分为不同的层次,不仅在边远地区的政府和军队,通常也有相当高层次的剧团,在各军区分和各县也有自己的剧团和剧社。 这些剧团分成小演出队下基层演出,他们帮助训练村剧团。 整个延安时代,由青抗先和文救会组织、各地乡土戏曲爱好者参加的村剧团一直很活跃,仅晋察冀边区就有村剧团上千个,它们的活动遍及边区的各个角落,也渗透到了敌占区。 因为这一时期延安政治的首要目标是建立民族国家的认可,在这些戏剧活动中,民族主义的激励占据了最突出的位置。 除了一些古剧外,还出现了许多现实斗争的真人,通过各种文艺形式的演出和推广,塑造和升华了形象,使得本来就很普通的事件迅速英雄化,让农民也可以把自己本来的行为像古代的英雄豪杰一样传唱 使之产生前所未有的自豪感,使农民意识到自己抗日行为的意义,意识到可以获得原有的开垦地和公共粮食,并且在发扬民族主义时,还会受到对民族背叛和害怕死亡的贪婪行为的谴责和鞭策。 在新老民族主义戏曲交替上演的情况下,现实中的汉奸与秦桧、潘仁美联系在一起,成为超历史的反对者。 这种方法向落后分散的根据地农村注入了现代这样的民族国家意识,逐渐确立了对共产党政权的阶级认同,为未来更加激烈的现代革命奠定了比政治基础更重要的文化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延安文艺的普及归根到底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大众化的目标是大众化。 民间戏曲归根到底是下层社会的产物,不识字的艺人和不识字的农民把浓厚的乡土观念带入了戏曲故事中,这既是忠臣义士的剧目本身,也缺乏绝对主义的意图。 因此,从借用民间文艺形式到改造民间文艺形式、重建民间形式,歌剧《白毛女》可以说是延安大众化文艺运动的高峰期,是这场运动的必然终结。

就主题而言,歌剧《白毛女》的改编和演出是抗战结束后,民心所向决定中国何去何从的大问题。 据说这部戏把中国看成阴阳双天,而且有生活原型,不知道真假,所以被看成是推进战中的重磅炸弹。 《白毛女》成为受解放区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剧目。 解放区的报纸不断报道当时演出的盛况。 每次到精彩的地方掌声不绝,经久不息,每次到悲伤的地方,台下总是能听到叹息,有人从第一幕到第六幕眼泪不停… … 戏结束后,人们都相互称赞。 称赞这是一出在舞台下感情融和的翻身人翻身的戏,同时充分肯定了它在实际斗争中的作用。 《白毛女》向我们提出了目前中国急需处理的土地问题。 杨白劳的死和喜儿的苦难,是农民没有土地和民主政权的结果。 所以今天我们要出版和公演《白毛女》。 那是非常适时的。 一个村子在看了《白毛女》的演出后,马上开始了反霸斗争。 一些部队观看演出后,士兵们纷纷要求杨白劳、喜儿报仇,掀起了杀敌立功的热潮。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读过《白毛女》后,写下了对自己阶级感情变化的重要影响。 《白毛女》在土改运动和解放战争中,一一发挥了艺术作品的感染力。 一部剧能在千几千万的群众中起到这样大的教育作用,在现代文学史上是空前的事了。

中共中央高层对歌剧《白毛女》的三点意见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黄世仁应该枪毙。 中央还特别说明了这一要求。 农民是中国的最大多数,农民问题就是农民反对地主剥削阶级的问题。 这部戏反映了这个矛盾。 抗日战争胜利后,这场阶级斗争必然尖锐,这出戏既然反映了这一现实,一定很快就会流行起来。 但是,黄世仁这样无恶不作,不枪毙他是不恰当的,广大群众一定不会答应的。 这个指示预示着中央政治文艺政策的转变。 这样的转变不仅意味着抗战中的租赁减薪和团结地主共抗日的政策将被土地革命和打倒地主阶级所取代,而且预示着更大革命的现代风暴的到来,摆脱了延安文艺对以前流传的意识形态的借用,成为表现民族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歌剧《白毛女》是延安文学的最高峰,也是延安文艺的终结。

江青把样板戏的成功归因于所谓的三方结合。 抓住创作的关键是领导者、专家、群众的三方结合。 具体步骤如下:先由导师出主题,再由剧作者生活三次,写好剧本后参加剧本讨论,广泛征求意见,然后再改,不断征求意见,不断修订。 江青的这段经历显然从延安文艺中偷了教师。 以歌剧《白毛女》创作为例,鲁艺领袖、理论家周扬从白毛女的民间传说中,敏感地发现和明确了歌剧《白毛女》的思想主题。 之后,作家、艺术家按照这一确定的意向,设计故事、编故事、塑造人物、结构、创作音乐,在编制过程中,从领导到炊事员、编剧、演员都正式上演后,鲁艺又按照中央领导的指示,编撰了一些重要情节。 在之后的公演过程中,在不断听取大众意见的基础上,反复进行了编撰、加工、润色。 《白毛女》可以说开创了文艺创作和艺术生产的组织化、计划化的先河。 样板戏的生产过程,无疑就是这种三结合形式的展开。

从艺术的形式来说,歌剧《白毛女》开创了对以前流传下来的戏曲进行现代改造的方法。 《白毛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洋歌剧,而是集戏剧、音乐、舞蹈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 歌剧《白毛女》音乐的创作者马可、瞿维如下说明了他们对这种艺术形式的理解。

中国古老的歌剧范围广,种类多,作为封建社会歌剧艺术的最高形式,包括早已衰落的昆曲、曾经被宫廷传诵至今仍在城市中流行的京剧、以及北方各种各样的拍子剧等。 虽然它们在戏剧音乐形式方面发展迅速,艺术水平也越来越高,但这种形式和它所表现的封建复制品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不能让它偏离…

鲁艺音乐工作者对以前流传下来的艺术形式的认识体现在歌剧《白毛女》的改编中。 因此,无论从主题还是形式上来说,歌剧《白毛女》都不再是以前流传的意义上的戏曲。 歌剧《白毛女》采用民谣、小调、地方戏曲的曲调,但既不是民间小戏的扩大,也不是以前流传下来的夹板或宫戏,而是参考西洋歌剧或戏剧侧重表现人物性格的解决方案,采用富有民族风味的音乐曲调在剧中上演 例如在歌剧表演中,《白毛女》借鉴了古典戏曲歌曲、咏唱、道白三者结合以前就流传下来的东西,特别是稍微吸收了陕北以前流传下来的秧歌的好处。 秧歌这种产生于农村环境下的民间艺术形式,具有单纯朴素的优势,以舞蹈歌唱为主。 原始的秧歌,连故事的复制品都没有,也缺乏戏剧的元素。 农民在农忙季节之余,仅靠发泄感情,常常表现出男女的体恤之情。 这也是因为被称为骚情秧歌。 鲁艺的作家大多是熟悉西方戏剧形式的现代艺术工作者,他们逐渐在秧歌的形式上加入了简单的故事和情节,带来了从秧歌到秧歌在某种意义上戏剧化的歌剧的迅速发展。 从秧歌剧《刘二起家》、《兄妹开荒》、《刘永贵受伤》到秧歌剧《周子山》,他们在歌剧《白毛女》的创作中积累了经验。 《白毛女》大胆采用戏剧的表现方法,展现了广泛而丰富的现实生活副本,人物对话使用戏剧的表现方法,观察和学习戏曲中的对白。 道白与歌唱的关系,是用来用歌唱叙述事物,回忆历史,介绍人物,烘托气氛,在感情需要爆发的时候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这些混杂的艺术手段产生了非常奇特的艺术效果。 当时人们就《白毛女》的艺术成就高度评价《白毛女》的演出是对中国歌剧迅速发展的最大贡献,最大的功绩就是其最高价值。 从这次公演开始,我们知道了如何从中国现有的歌剧形式中学习、吸取,如何将旧的和新的联系起来。 从初期开始,《白毛女》借用之前就对民间艺术进行了大胆的改造,这表明革命文艺经过以普及为目标的延安时期后,开始回归到提高这一现代性的启蒙目标上。 文学艺术的创造者不再像以前那样尊重已经存在的艺术了。 这种将古老的东西为现在、将西洋用于中国的创造欲望,不仅会出现在未来的艺术实践中,也会出现在政治实践中吧。 其中的一个标志,当然是文革文艺的典型示范戏。

如何解决以前流传下来的形式与现代革命的关系,是革命文艺最重要的课题,当然也是现代性带来的问题。 文革后为数不多的样板剧研究成绩微薄的原因之一是,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文革文艺,并未被置于20世纪中国现代成长的历史中加以整理。 因为这么多问题容易混淆。 实际上,样板剧这门艺术政治学绝对是现代成果,如何利用和创造以前流传下来的问题,是五四时代挥之不去的时代命题。 在五四以来延续到30年代的俗文学运动发掘和发现民间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认识到历史悠久传承下来的艺术形式在落后的农村生活中对农民的思想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改良了这些古老的艺术形式,加入了新的文案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手段,将文艺作为 这样的构想体现了知识分子对作为他人的民间、自身启蒙和社会改造作用的现代想象,显然不能理解为农民文化对知识分子文化的否定,也不能理解为对以前流传下来的五四的否定。 围绕抗战时期、旧形式民族形式的利用等问题,文化思想界对毛泽东、陈伯达、周扬、茅盾、胡风等各种论述反映了对新文化走向的认识,其中当然也涉及延安文艺的文艺资源问题。 其中茅盾的观点具有代表性:

旧瓶子装新酒并不是利用旧形式的全部意义,如果是全部意义上的话,应该说是应用旧形式而不是单一利用。 利用有两个意义。 应用旧的形式,带来了所有的间借。 例如,应用京剧这种形式,连台步的脸书都拿来了,瓶子完全旧了。 瓶子的旧招牌也完全不动,只是借用肉体的方法,可以说是初步手续,但显然不能使用。 所以,更旧的东西是不可缺少的。 所谓推出新事物,就是去除不适合旧现代生活的部分,只留下其表现方法的精髓来补充新事物。 以京剧为例,可以保留歌剧的特色和象征方法的特长。 (例如,用帘子代替城堡,用马鞭代替马等,不是现代服装、台步、脸书等,可以去掉。

茅盾显然把陈新视为利用旧形式的最高目标。 这几个既是延安文艺的目标,也是文革文艺的目标,还可以看作是五四文艺的基本环节。 唐小兵说延安文艺有其历史必然性。 理由大概就在这里。 因为延安文艺的大众化目标是五四文艺的基本主题。

在现代中国,大众文艺的实践及其最宏伟的表现,是我们现在必须认真考察的延安文艺。 在延安文艺中,由于一直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孕育,30年代确定表达的群众意识得到了实现的条件和体制上的保障,群众文艺由此完成了自身逻辑的发展,同时有序化、政策化。

如果承认延安文艺和看起来对立的五四文艺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也许可以从另一个意义上理解延安文艺和文革文艺的关系,甚至可以促进在文化革命意义上重读20世纪中国的政治革命。 从而加深对永恒不变的现代历史的理解。
正如公开的革命已经不是定时的事情,革命之前在整个社会生活过程中使用的无数日常斗争和阶级分化的形式潜伏在前革命的社会经验中,只有这一真理的瞬间作为后者的深层结构出现一样,文化革命公开过渡的瞬间本身也在人类社会中。 因为,新制度主导因素上升的胜利瞬间,不过是它为了永远保持和重生自己的主导地位而不断斗争的持续表现,这种斗争在其生存期间必须一直坚持下去,在所有时刻都拒绝同化,寻求支持 在这最后的视野中这样理解的文化和社会解体的任务,显然是改写其素材,从而理解这场永恒的文化革命,解释为更深层、更持久的构成结构,也理解在这个构成结构中经历的拷贝对象。
本文:《“文化革命”视野中的“延安文艺””》
心灵鸡汤:
免责声明:学习兴国网免费收录各个行业的优秀中文网站,提供网站分类目录检索与关键字搜索等服务,本篇文章是在网络上转载的,星空网站目录平台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只为传播网络信息为目的,非商业用途,如有异议请及时联系btr2031@163.com,本站将予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