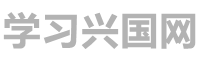“她们除了叫母亲之外,还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历史”
一座牛栏山,几块父亲卤肉牛肉。 这是对母亲来说最舒服的下午茶。 在田地和厨房前长大,能吃能喝,是她从小辛苦劳作的副产品。
母亲出生那年,在家里被命名为美。 毛主席语录刚开始印在教科书上。 上学后,小美学习勤奋,成绩优异。 雨里泥泞不堪,满地都是牛粪、泥水、奶交融,她也光着脚,忍着浑身的鸡皮疙瘩,跑向学校。 多才多艺的她作为文艺推进队的骨干,就这样在周边的乡村公演驰骋。

花五分钱吃红薯,写命题作文,小美考上了乡下的中学。 开学不久,祖母到了学校,裹着被子回家。 并不是因为家里穷不能上学。 我爷爷是乡镇干部,家里有汽车,粮食年产几千斤。 但是,作为长女,她被认为承担着全家7口劳力的控诉。

美小姐早就预料到要辍学,打算自救。 每天去学校先下地,捡书包里的大豆回家,怕奶奶说那句话。 这一切终究是徒劳的。
祖父工作很忙,祖母需要得力助手。 阿姨顽固笨拙,挨打无数。 两个叔叔被送到国外读书,但什么也做不了。 大胆且吃苦耐劳的小美成为了支撑家庭的最佳候选人。
人不过是锄头高的小美彻底成了家里的第一劳力。 割麦子的季节,我阿姨和伙伴们玩,叔叔两个人在地头乘凉,祖母回家做饭。 这一瞬间,小美成了麦田里孤独的守望者。 一个少女的模样在黄土地上勾勒出前弯的样子。
爷爷永远有吃不消的客人,每年的粮食一年到头都吃光。 妈妈每天都要摆摊和收摊,勺子无数。 他们习惯了在旁边喝一杯,喝一杯,她也养成了从来不吃剩饭的习惯。
从十几岁开始,小美就学会了和父亲一起喝酒。 因为这是消除疲劳的唯一方法。 她父亲今年快70了,午饭、晚饭两瓶白酒依然保留着,这大概也是小美的现状和未来。
在干燥炙热的厨房里,在晒黑的天地之间,小美的青春。 交给劳动,交给怨恨,但永远在意没能去学校。 几年后,祖母说对不起母亲,后悔没有送母亲上学。 听了这句话,母亲脸上毫无波澜,只是后悔一句,无济于事。
父母是通过相亲认识的,两个村子隔着一条河。 父亲是村子大门的大户,家里只有有地没钱的穷地主。 他作为家里的次子,曾被送到无法抚养的叔叔那里。
结果,叔叔总是来儿子,终于爸爸有了人生,没有人抚养,成了连生日都不知道的野生孩子。 他从来没去过学校,从小就和石油工人混在一起,早就有了社会氛围。 也许是这样的痞气吸引了妈妈。
24岁出嫁时,她步行去了父亲身体挖地基建的三间平房。 等待母亲的不是新的生活,而是一成不变的劳动和饥饿。 叔叔俩背着粮食来过我家帮忙,妈妈也捡过石油工人扔的白菜叶放进锅里。
更绝望的是歧视和无视。 婆婆们拒绝借给妈妈五块钱,带着我过了一会儿,让妈妈可以用空做饭吃。 这对贫穷的夫妇仿佛不是那个家庭的一员,甚至借钱养羊最后也被偷了。 无数人在背后指着后脑勺,摆出一副天不怕人的架势。

为了谋生,妈妈尝试了所有能做的事,但从来没有离开过家。 她一直陪在我和姐姐身边,看着我们长大成材。 妈妈推着棚车到周围的乡下卖水果,半夜背着近百斤石油,卖雪糕,开店。
自从我写完文章,妈妈的样子只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剩下的时间我和姐姐被关在家里,晚上已经睡了,她还没有回家。
小学的时候,父亲去武汉打工过半年。 那也是他唯一的兼职经历。 那半年,家里几亩地完全交给妈妈一个人,麦子收的季节,妈妈把老家所有人都叫来,收割,装车,在道场打麦子,最后运输回家。
回家后,妈妈经常做饭招待大家。 我蹲在堂屋的门槛上,看着一屋子人坐着吃饭,妈妈额头前的几缕线在空的气息中勾勒出坚强的身影。
在三间平房里,我从没注意到过家里的贫困。 我总觉得家里情况和周围一样,日常零食丰富,过年杀猪宰羊; 丰收季节,全村一起面对黄土,一起喝啤酒,分享小流行音乐。
我小学的时候的一个夏天,父母外出,为了不让姐姐和我太热,谁都不会变暖,家里的旧冰箱里装满了冰棒。 后来我才知道,父母竭尽全力让我们衣食无忧,让我们除了学习以外。
我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在家里盖了新房子。 据母亲说,盖房子时,家里的存款只有5万美元,但在盖房子的过程中,父亲积攒了十几年的人品突然爆发,成为了家乡中石油分企业建设的小承包商。
那一年,妈妈不仅呼唤了一个人盖房子的过程,还每天做两大桶饭,背在工地上,并且用自己最重要的小学知识,晚上记账在爸爸的工程上。 之后几年,妈妈白天做建筑工人,晚上记账。 她记性好,记账牢固,每年所有的账目都分不开。

人很闲,指甲很长,心很闲,头发很长。 但是岁月终究不留情面,妈妈的小手,虽然还没有皱纹,但还是从12岁开始和锅碗瓢盆摩擦,月入冰块水洗尿布,拿着镰和锹,抓着茶叶和菊花,摸过石油和水泥。 几根手指变形,接触冷水后疼痛异常; 双脚也站着、走着、跑着,所以得了静脉瘤,好多年都不好治,不能经常走路。 结果身体不舒服了。

我们村不大,本来土地就少,靠着石油分企业占地的补偿,村里的人也凑合着过。 但是,在这期间,地里的粮食越来越不值钱了。 农民工回家的村民们带回了令人惊愕的财富。 村子里的一部分田地种在树上,打工的人更多。 到这两年为止,在村里除了父母以外都在守护着,几乎都是空。

过年的时候,多嘴多舌的妈妈也不想出门了。 大家多年没见了。 见面后,在客套话中,言语之间总是互相比较。 妈妈经常说,这个时代是好是坏,曾经大家一样穷,吃饭的时候,拿着碗聚在村口,笑啊笑啊。 现在大家都富裕了,但总有差距。 在那里,好像是拼着你的死和我的命活着。

艾伦是我妈妈。 作为家里的长女,她6岁的时候被送走了。 那天和往常一样,她和旁边的几个玩伴一起上山打猪草。 她背着一筐比她还重的猪草在黄昏中回家时,阿姨已经坐在家里了,桌子上放着布包袱。
我祖母对她说了。 “艾伦,从今天开始去阿姨家住吧。
姑姑的婆家在河对岸,夫妇结婚十多年了,一直不能生孩子。 父母嘴上说阿姨家离小镇很近,但是很容易去学校。 但是作为长女的艾伦心里明白,家里有两个哥哥,两个刚出生的弟弟和妹妹。
她一直都是自己的错,谁让自己家穷? 她责怪自己努力不够,工作不够。 请回想一下。 艾伦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 在几个哥哥的陪伴下,度过了几年的童年。 毕竟,在她熟悉的这个村子里,给没有孩子的亲戚送女儿是常有的事。 而且,该村的莲妹妹不到2岁就被父母作为媳妇送到邻町的家人那里,一年几次都没能见面。

那天,祖母破天荒地炒了一碗白菜。 几个大叔在旁边看着,一个也没动。 如果放在平时,一杯白菜,三个孩子动几根筷子,连汤都没了。 艾伦至今还记得一大碗白饭。 从小就没吃过这么多饭,时隔几十年,艾伦朝已经颤抖的祖父母喝了酒,在家里的宴会上笑了起来。

在亲戚们开着新话题的时候,艾伦低下了头,擦着眼角流下了眼泪。 仿佛又想起了那几年所寄身的生活。 艾伦在阿姨家开始上小学。 与自己不识丁的父母相比,姑姑是村干部,膝下无子,自己也还照顾着他。 除了工作日在阿姨家干农活外,一到农忙期艾伦就必须回家帮忙收割。

小学4年级那年,阿姨生病去世了。 爸爸不到几个月就娶了另一个妻子,对艾伦的态度越来越冷淡。 小学5年级的时候,阿姨的弟弟收养了儿子。 这次,艾伦又被送来了,因为阿姨觉得家里孩子太多了。
回到村子后,她总是害怕自己会被再次送走。 周围的亲戚有孩子和女儿,如果再送走的话可能会去很远的地方。 为了让自己更有用,她在努力学习。 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学习好的孩子。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她就是全村最会读书的孩子。 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早早在祠堂里占了好位置,等着播电视,但她决不去。 她的习性是在灯下读完所有自己能找到的东西,才十岁就成了家里唯一深近视的人。
之后,艾伦来到镇上上了中学。 每周末回家,祖母都会给她准备一些自制的腐乳。 那是她一周的菜。 多年的婚姻和生育后,艾伦每天吃很多菜,饭和腐乳。 她说要把小时候没吃的菜拿回来。
艾伦的成绩一直很好,但升学时给全家带来了灾难。 我妈妈一般考上高中,没有钱只能读中专。 祖母擦着眼泪对我说。
中专毕业分配工作时,家里无关,所以成绩优异的艾伦被分配到了偏远的工厂医院。 成绩中等的室友几个反而进入了市级大医院,毕业后进入了不同的人生。
工厂的工作很辛苦,但是艾伦第一次有宿舍,领工资,相亲后找到了对象。 这次,她终于不能再送了。 结婚后,工厂把她从单身宿舍搬到孩子的母亲中间。 夫妻俩买了两把竹椅。 那是唯一为新婚买的家具。
在其下海和下岗一样流行的年月里,艾伦的工厂改建了,工厂医院快半年没发工资了。 那年我小学二年级,她带我去书店买了补习资料。 每个科目的习题和读本加起来需要100元。 当时一个月工资300元的她左右为难地捡起来,留下了50元。 在回家的路上,她一直责怪妈妈没用,买不起书。

之后,公司卖给了私人业主,但工厂医院的问题迟迟未能得到处理。 由于没有交接单位,工厂想把医院转交给个人承包。 艾伦就这样被再次送走。 但是,谁能看到边远工厂的小医院呢? 在那之后的几年里,这家小医院只能自负盈亏。 她也经常工作好几个月没有工资。

妈妈的半生就这样被送来了,就像个多余的人。
一个夏天的晚上,她发现了丈夫外遇的痕迹,叫来了周边所有的亲戚。 我第一次看到她那么歇斯底里。 我错在哪里,我错在哪里,她对着屋子里的男人咆哮。
谁也不应答。 几个亲戚在旁边拉着她,想着面子和孩子,想开一点。 前面开朗倔强的她,那时那么无助,没那么多选择。
其实她什么也没错过,但永远在责怪自己。
妈妈叫荔英。 是铁的女儿,1958年出生。 那一年,全国开始大跃进,很多男人做不到的事她都能用手抓住。 小时候,我拿着碗,看到电饭锅被打开,妈妈空手快速进去,拿出不锈钢浴缸,匆匆放在餐桌上。
之后,她向我解释了。 我做了二十年硫磺化工,早就掌握了抗热的能力。 这些不过是儿科。
那一瞬间,我不得不承认,我不知道该怎么写硫化,甚至不太了解妈妈。
她18岁进入橡胶工厂开始硫磺化工,每天穿着工作服、工作帽、手套武装,忍受着4、50度的室温工作。 为了保证机器的温度,工业落地式电风扇只能从很远的地方吹,无法阻止来自机台的热浪。
消暑茶对这家的女性来说是唯一的防暑工具。 整天汗流浃背,连内衣都湿了。
妈妈说她的车间很大,还没走到一半的位置,就看不见站在前门的人了。 车间里最显眼的是各种机器和模具,排列整齐,又重又硬。 人站在前面又小又脆弱。
一不小心,有些同事擦在机器的喉罩上,发出咣当一声,皮肤变红了,肉也熟了。 这个小伤疤很常见。 家常便饭。 请以为机器吻了你。 以及… … 被机器划伤手指的人,没戴员工帽的人,被粉丝拉头发的人,妈妈咚咚咚的人,不说这些,总之很多人都被皮肉折磨着。 因为过去的话题才刚刚开始,妈妈怕自己说太多,马上转移话题,不想再详细考虑。

荔枝英在珠江三角洲某市西郊的一个村庄长大,工作。 父母都是藤厂的员工,家人很多,生活并不轻松。
快八岁的时候,荔枝英才要上学了。 学校的老师来拜访,说全员都要去学校,不能不读。 她背着患有严重哮喘的弟弟去学校,坐在教室最后一扇门的角落里。 弟弟一哭就哄,一哭就哭,去外面的沙地,停止哭泣回教室学习,为了做作业做完了很多家务。

那时的荔枝每天往山上劈柴,用镰刀割草,在河水涌出的地方摸蚬贝。 冬天零下几度,寒气凛冽,手脚麻木。
上高中申请的时候,荔枝英已经17岁了,超过了入学年龄。 因为家里很穷,所以没有自然地继续读书。 于是她一边等待分配工作的通知,一边在家帮忙工作。
那是文革后期,在祖父祖母工作的藤工厂招募家人。 荔枝英没有学习,要当元军。 每天的工资是一人两毛一天,所以做简单的助理业务。
大半年过去了,只有荔枝英还没等指派,当时很慌张。 去劳动局查了一下,发现文件落在抽屉底部,最后只能分配到离家半个小时左右的橡胶厂。
刚入职的时候,刺鼻的橡胶气味让荔枝英完全受不了。 她每天头痛,眼睛滴水,为此闷了很久。
生命啊。 运气不够,开始造势就输了。 妈妈叹了一口气。 读书是这样的。 员工分配也不顺利,工作地点不好… … 她的小眼睛看着电视,厚厚的双眼皮下垂,纤细的短睫毛眨眼,很寂寞… …
啊,总之很悲惨。 反正做着做着就习惯了,是环境改造人。
橡胶硫化工行业是高温有毒有害的特殊工种,按照国家规定,女职工45岁即可退休。 过去,她有信心45岁就能坚持到退休。
但是,辛辛苦苦而怀恨在心的荔枝英,在42岁的时候没能在收发的职场上支撑住。 她的腰一直剧痛,痛得连鞋都穿不上。 管理员建议她去看医生,发现她是腰椎间盘突出症。 她辗转多年的医生,尝试了所有的中西药、针灸复位、盲人按摩。

作为经验丰富的一线工人,荔英在将近40岁的时候,有工人出口的机会,去日本工作了两三年,赚了美元回来,不知道有多过瘾。 但是,因为父亲长时间在外勤,所以为了照顾年幼的我,她不得不调到全日班的收发办公室。
那几年,她戴着又重又热的手套,一天运几千斤的橡胶材料,养育了我。 2003年,两次调职的荔枝英终于忍受到了正式退休。 一年后,橡胶厂倒闭了。 很快,她从小长大的藤工厂也倒闭了。 荔枝英和父母流着青春汗水的地方,一眨眼就成了陈迹。

20年前,接待处的荔枝上,月经提前了一个月,一个月提前了几天,最后提前了18天。 经期长,量多,有时一天换七八张卫生巾,还充满气味。 现在,想起往事,她毕竟觉得自己身体素质不够。
现在,时间逐渐填满了两个工厂。 西郊的那个区域,河涌农地变成了道路,不动产财团强势进驻,搬到山上祖坟,地铁开通,村民开始抢夺住宅建设… … 母亲和祖母两代铁娘的过去,随着时间的流逝,故乡也渐渐模糊了。

几年前,市里开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但即使离家乡稍远,也有人利用新正头热闹一下。 每当想起去世的故人时,妈妈总是感到有点悲伤,这是噼里啪啦的声音,很遗憾。
月阿姨是妈妈的同事。 下岗那年,她到处交资料,要求处理工龄问题。 问题马上就要解决了,她却突然死于内脏衰竭。 那时,她忙得照顾不了身体,一时下班没钱也舍不得看病,非常遗憾,妈妈叹了口气说。
我记得正好在那年年初,她们关系很好的姐妹们一起在家里的阳台上看了新春辉煌的烟花大会。 空中一个火种变得四分五裂,短光照了夜晚之后,是漫长的沉默。
美,艾伦,荔英,这是她们的名字。 是的,她们除了被称为母亲外,还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历史。
正文和封面的图最先以土逗开始。 转载请联系土逗获得复印许可。
作者:理识平吴碧莲陈之
:小蛮妖
美编:小永
本文:《“她们除了叫母亲之外,还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历史”》
心灵鸡汤:
免责声明:学习兴国网免费收录各个行业的优秀中文网站,提供网站分类目录检索与关键字搜索等服务,本篇文章是在网络上转载的,星空网站目录平台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只为传播网络信息为目的,非商业用途,如有异议请及时联系btr2031@163.com,本站将予以删除。
下一篇:“在苏联的生活好吗”